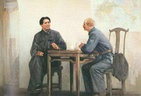算钱不算人——从技术角度说国民党政权的失败

中国史家自太史公司马迁以来就有一个很不好的毛病,关于历朝历代的王朝兴废,偏好于评论领导者的有道无道、有德无德,却鲜有从技术角度梳理历史脉络。而不去考虑天下经略,空谈道义,且不说立场如何,最终都难免执着于小德而不见大道,也让“以古鉴今”无从谈起。
在迄今为止我们的绝大部分历史时期,任何一个相对完整的权力体系,当然也包括国家这个最大的体系,无论具体构成如何,在社会结构上其实都大同小异——都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级:最上层的权力核心,过去很简单,就是君王,到了现在由于权力的分散,界定起来比较困难,但还是可以划分出来;中间的精英阶层,包括官僚集团、知识分子,农耕时代的地主豪强,工商时代的资本家;下层则是普通民众。理论上说,只要信息的传递与处理存在“时间差”,中层就是连接上层与下层,组织社会力量从事生产必不可少的环节。国家管理可能离我们的生活比较远,但企业管理大伙还是不陌生的,由于精力有限,且随着买卖越做越大涉及的专业只是越来越多,作为决策层的董事长和其他大股东肯定不可能事必躬亲,正在管理企业运作的是CEO和他下属的各个部门经理所组成的管理层,如果这个“企业”叫做“国”的话,那么这个执行层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精英阶层。
中间阶层必然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而其所处位置与构成又决定了这个阶层相对于上面一层有数量优势,而相对于下面一层,又在人员素质和资源控制上有质量优势。一旦社会体制对中间一层的自我膨胀失去控制,则社会结构便会趋于畸形。回到上面的那个例子,在大企业里,决策层和管理层间的博弈往往是一个贯穿始末的主题,而众多企业的衰败,也恰恰是由于决策层失去对管理层的控制所致。而国家说到底也是这个道理。孙权和张昭的故事相信大伙都不会陌生,再通俗点就是“县官不如现管”,张昭们的“现管”的位置决定了,即便孙权这个“县官”被曹操替代了,于他们而言利益基本也是无损的,甚至改朝换代还能带来额外的收益。
因此从“治人”的角度说,居于权力高层的领导者最明智的取向应该是联合下层民众,以其对中间的精英层进行监督,以此达到整个权力架构的均衡。但如果以“算钱”的角度来说,则你会得出一个截然不同结论:从成本角度说,收买数量较少的中间阶层,由他们代为管理民众,显然要比“收买”民众的成本要低得多。而进一步说,尽可能控制这些支持者中“核心成员”的数量,同时保有一部分外围“候补成员”,则可以进一步降低成本,同时给“核心成员”以压力,以保证其忠诚度。于是乎,我们便看到了四大家族,看到了国民党内派系林立相互倾轧。这既是国民党政权的弊端,可又是它能得以存在的保障。如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1948年国民党政权的存亡已在旦夕之间,而蒋经国在上海的铁腕“打虎”不过70天就无果而终。不仅对于中间精英层如此,对待基层依旧如此——将基层管理“承包”给地方豪强从成本核算上说同样是合算的,蒋介石在其所着的《中国之命运》中便对“绅宗自治”夸赞有加。如此当时的中国基层就形成了“包税制”,即国家力量不接触基层,而把管理权交给地方豪强,上级管理者只负责定时定量向基层管理者收取税款,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的“承包制”,承包工厂是为了赚钱,承包权力自然也不会例外,在定量上缴数额之外,多收一块,自己便多拿一块,由此往下想,基层平民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由上至下层层“承包”,也就意味着即便只考虑国家运作的正常财政需求,最初的所需数额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层层加码,最终重重地压在老百姓身上,并将他们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去。
如前文所说,20世纪初是左翼思潮席卷全球的年代,当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甚至早于美国半个世纪允许工人用罢工权,经济上强调国家意志主导和财富均衡分配并非只是苏联的专利,美、意、德、日、法、英等国其实都在搞,无非是步子迈得早点晚点、大点小点的区别。北伐时代的秉承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其经济思维基本也是这个框架的影响下。所以国民党才会接受到苏联的大部分援助,同时才会在苏联的牵头下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对其最大的作用就在于强化了国民党的基层组织能力。“4·12事变”之后,国民党不光屠杀了大量共产党员,也干掉了自己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基层组织[1]。而从经济思维角度说,蜕变后的国民党政权的思路便走到了上面那个模式上来,而这和当时全世界的总体潮流完全是相悖的。
1930年以后,随着北方战事的逐步平定,民国进入到了平稳建设的所谓“黄金十年”。本着“收益最大化”的原则,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精英们把绝大部分资本都投入到了东部沿海一线。而对于国家根本的中西部特别是农村地区却少有顾及,这就又丧失了一个强化国家政权控制力的机会。而自甲午战败之后,中国东部早可以说是“有海无防”,从战略安全角度说,这就像一个人的心脏长在身体外面一样危险。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日本人曾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当时“灭亡”所指的就是中国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命脉,而这些当时又都集中于沿海的那么几个地方,所以说日本人的这个“海口”夸的其实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1937年8月一场淞沪会战,国民党“黄金十年”的成果便损失殆尽(当时大部分工业设施都未来得及迁走)。
而宋子文那句“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说到底这就是一种“算钱不算人”、“算钱不算国”的思维模式。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战争开销,开始发行金圆券,强行兑换老百姓手中的金银外汇,结果“尽收天下之财,皆失天下人心”,随着金圆券无节制的滥印,国统区物价飞涨,国家信用体系实质上已经宣告破产。
在同一年的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开始发行人民币,当时人民币不与金银本位制挂钩,也不与任何国家的外汇挂钩,而以人民政权的信用为担保。而在此之前,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即城南庄会议)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会议的议题归结起来就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那句着名的口号:“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而这其中的“加强纪律性”,实质主要是指强化财政纪律,适度缩小地方政府权力。而这可以看做是为人民币发行在做前期准备——强化财政管理,减少财政赤字才能尽可能避免倒逼造成货币滥发,如此人民币的币值才能保证稳定。到战争后期,由于人民币事实上是和粮食挂钩的,且币值较为稳定,为了吃饭,众多国民党地方政府都必须储备人民币。战场上决战已经展开,而在金融上,胜负早已分晓。后来所谓“共产党军事上一百分,政治上八十分,经济上零分”,说这话的人对经济的理解恐怕才是真正的“零分”——精其术,却不得其道。不是零分,又能是什么呢?
[1].从这一点看,国民政府根本不可能破除包税制。
【察网摘自王伟《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50万册纪念版全新修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赞同、支持、鼓励!」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