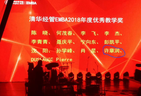美国刑事起诉华为涉嫌窃取商业机密案的分析
美国刑事起诉华为涉嫌窃取商业机密案的分析
华为前几天发布了5G芯片,从性能看是西方类似产品的两倍,功能上更是大大超过。华为5G基站安装简单,性能强大。华为还宣布将在下月发布折叠式5G手机。同时,华为预测将在今年或者明年超越三星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厂商。而昨天,美国司法部刑事起诉华为,其中一个案子是指控华为窃取 T-Mobile 一个叫 TAPPY的机器人技术。案件名为 USA v. Huawei Device,案件号为 C19-10,所在法院为华盛顿州西区联邦法院。下面我根据查阅相关法庭案卷获得的信息对该案进行初步分析。
基本案情如下。T-Mobile 是一个移动运营商。2006年左右,它设计了一个用于测试手机的装置叫做 Tappy. 2012年9月13日,T-Mobile 公开了 Tappy 的视频 (参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v69ZxKOFSw&t=10s)。从这个视频看出,Tappy 是在 EPSON的一款机器人上安装一个橡皮头在手机屏幕上点来点去。这样代替人工测试,据说可以大大提高效率。EPSON的这款机器人型号叫 SCARA,市价约七千多美元。显然,EPSON SCARA 机器人不是什么商业机密,更不是 T-Mobile 的商业机密。至于用机器手测试手机,这也不是什么商业机密 -- 自己都公开放网上了。T-Mobile 发布的这个视频是高清的,还包含了 Tappy 的设计图:就是在 EPSON机器手上装了个橡皮头。Tappy 的商业机密也就是这个橡皮头。更具体的说,指控华为窃取的商业机密是这个橡皮头的大小与材料(注一)。
华为在2012年跟 T-Mobile 签订了一个协议向 T-Mobile 提供华为手机。但是 T-Mobile 在用 Tappy 测试华为手机时,很多时候不能产生触摸反应( 原因其实是 Tappy 并不能模拟手指触摸,见后)。华为的工程师于是向T-Mobile 索取 Tappy 的相关数据。T-Mobile 拒绝了。2013年5月,华为美国分部的一名工程师在 T-Mobile 的实验室进行测试,T-Mobile 给了他四个橡皮头。该华为工程师未经允许将其中一个橡皮头拿出实验室,对其大小进行了测量,并将数据报告了华为。
T-Mobile 随后在华盛顿州西区联邦法院起诉华为非法获取 Tappy 的商业机密,索赔一亿多美金。但经过10多天的审判,美国陪审团在2017年5月17日做出了一致裁决:1)T-Mobile 因为华为不当获取商业机密的损失为零美元 ($0);2)华为因为不当获取 T-Mobile 商业机密的获利为零美元 ($0);3)华为的行为不是“蓄意与恶意的”(因此不需要支付惩罚性赔偿)。另外,T-Mobile 还起诉华为违法合同,索取违约损失,包括寻找华为替代产品的增加成本等,陪审团对这个违约部分裁决华为需要支付480万美元赔偿。
陪审团等于说那东西一文不值。审判结束后,T-Mobile 对陪审团的裁决不服,提出要求重审。而华为认为证据足够说明侵权赔偿为零的裁决。从双方的法庭辩论中,我们获得了相关案情的大量信息。
原来,早在2012年,一个名叫 William Wevers 的第三方专家就对 Tappy 进行了检测。他发现 Tappy 的橡皮头过于坚硬 (overly rigid)不能正确模拟人的手指,它按下去的力量过大,甚至可能导致感应器弯曲而屏幕失灵。T-Mobile的工程师自己也承认橡皮头得重新设计。这才是 Tappy 不能在华为手机上正确引发触摸感应的原因。华为自己也设计了一款测试机器人 xDR。两名专家 Dr. Smith 与 Dr. Wolfe 作证表示,华为的 xDR 跟 Tappy 完全不同 (“Tappy and xDR were completely different in almost every respect. May 11 Trial Tr. at 188:3-90:17, 198:2-99:5, 205:8-206:6, 208:10-16; May 9 Trial Tr. at 198:4-199:13. T”)对此,T-Mobile 的专家只是提出“功能等价”的反对意见。经过这一系列交锋后,T-Mobile 与华为在 2017年 12月达成了协议,将 Tappy 相关案件永久撤诉。而华为在2016年起诉 T-Mobile 侵犯华为 13 项专利(大部分为4G专利),案子双方也几乎同时达成和解。
粗略看了一下美国政府最新起诉华为窃取 Tappy 机密案,其刑事指控内容与 T-Mobile 对华为的民事案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基于以上基本事实(注二)。众所周知,刑事案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是犯罪意识,光是有行为是不够的。如果华为工程师只是为了弄清楚为什么 Tappy 未能正确测试华为手机,这根本不是什么犯罪意识。在 T-Mobile 对华为的民事案中,陪审团裁决华为不存在蓄意与恶意。民事案的证据标准是可能大于不可能,而刑事案的标准是“超越合理质疑”,后者是一个苛刻得多的标准。既然民事案的低标准都未能证明华为存在蓄意与恶意,刑事案的高标准应该更难以证明。现在问题是,华为能否用民事案的结果作为刑事案的辩护呢?
在美国法律上这叫做 collateral estoppel。简单的说就是用前一个案子中已经确定的问题狙击后面的案子,又叫称 issue preclusion,已经在法庭上打过的问题不许再打。具体到华为的案子,论点是民事案都没判存在蓄意,刑事案更不成立。
有个失火爆炸案造成一人死亡,US v. Egan Marine Corp. (843 F. 3d 674),美国政府先是民事起诉肇事公司,结果败诉。 民事案输了之后,美国政府再刑事起诉这家公司,结果赢了,被告公司被定罪。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推翻了这个结果:民事案低门槛都没打赢,怎么能赢高门槛的刑事?判决撤销。
当然了,US v. Egan Marine Corp. 案里原告都是美国联邦政府,被告都是Egan Marine Corp。Tappy 民事案的原告是 T-Mobile,刑事案双方与民事案换了一方人马, 法律上称为 non-mutual (非相互)。但是从 Egan Marine 判决的精神看,issue preclusion 的主要原因是民事案给出了判决的充分理由,而不是双方人马相同。
另外,我认为美国法律有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美国刑法很灵活,像上面的案子可以弄成刑事,司法部长、FBI局长、国土安全部十几号人一起大张旗鼓。
注一:从T-Mobile 公开的视频看,橡皮头非常清晰,有手机屏幕作为参照,单从这个视频应该就可以算出橡皮头大小。如果是这样,橡皮头大小也就不能构成商业机密。至于橡皮的材料,似乎没有看到 T-Mobile 发明了新材料,也没看到华为获取了橡皮的化学数据。
注二:美国政府的刑事起诉书中称华为员工拿走了机器人手臂 (robotic arm),这应该是不准确的。从 Tappy 的结构看只是一根棍子顶块橡皮,上面那一节不存在特殊性,也不需要替换。民事诉讼文件提到的只是“rubber tip”(橡皮头)。华为员工在四个橡皮头中拿走了一个。
tappy - 1.png
tappy - 2.png
华为涉嫌窃取商业机密刑案释疑
我这篇《美国刑事起诉华为涉嫌窃取商业机密案的分析》下有很多有价值的评论与疑问。下面我尽量回应。
1. 华为(美国)员工从 T-Mobile 实验室拿出来的到底是机械手臂(robotic arm) 还是橡皮头 (rubber tip)
从前文中我们知道,T-Mobile 用于手机测试 的Tappy 的机器人是EPSON 公司的商业产品,7000多美元一台。双方的诉讼文件中有一个 T-Mobile 2012年公布的专利申请(注意只是申请),申请发布号 2012/0146956 标题是“触摸屏测试平台”,正是这个 Tappy。该专利申请描述了这个机械手末端的材料,包括橡皮等等。这些公开信息都不是商业机密。
T-Mobile的民事起诉书里对事件是这么描述的,2013年5月29日,T-Mobile 给了华为员工 A.X.先生四个 "end effector" (“末端感应物”)在其实验室进行测试(Mr. A.X. ”was provided four end effectors for testing purposes in T-Mobile’s testing lab”(民事起诉书第54段) )。A.X. 先生把一个“末端感应物”放在其笔记本包里、拿出 T-Mobile 实验室测量了尺寸并报告了华为。民事起诉书并未指责A.X.进行了其他物理、化学分析。因此,华为被控窃取的商业机密就是这个末端的尺寸。
现在问题来了,“末端感应物”(end effector)是什么?机械手还是橡皮头?T-Mobile 的起诉书没有对 “end effector”一词进行定义。根据 Collins 英语词典(机械工程):“In robotics, an end effector is the device at the end of a robotic arm” 。也就是说,end effector 是机械手末端的装置,而不是机械手本身。更具体的说,应该就是下面图片中那个与屏幕接触的橡皮头。
tappy - 1xx.png
(以上图片来自 Tappy 公开视频截屏)
美国联邦对华为的刑事起诉书中似乎是描述同一件事情。刑事控告说2013年5月29日,华为(美)的A.X. 把一个 "robot arm" 放入其笔记本包中,A.X. 然后测量了 "the stolen robot arm" 的尺寸,然后报告给了华为。鉴于民事、刑事起诉书的惊人雷同,可以基本判断这是描述同一个A.X.做的同一件事,美国刑事起诉书中的“stolen robot arm” 与 T-Mobile 民事起诉书中的 "end effector" 是同一个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说,指控华为(美)员工拿走机械手应该是一个不准确的描述。至于为何如此?读者可以思考。
2. 华为(美)员工未经允许拿走东西是否构成“偷窃罪”?(什么是犯罪意识)
西方文明(至少从古希腊开始)很早就认识到了犯罪 (crime) 不光要考虑行为还必须有心理要素。一般来说,构成犯罪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涉嫌犯罪的行为(Actus reus),犯罪意识 (Mens rea),以及行为与意识的同步(concurrence )。直白的说,必须是带着犯罪意识的同时进行涉嫌犯罪的行为才是犯罪,三者缺一不可。不同类型的罪行需要的犯罪意识标准又不同。由此我们区分“一般意图“ 罪行(general intent crime)以及 “特定意图”罪行(specific intent crime)。如果这些概念略显抽象,下面我举两个例子说明。
以“打人罪”为例,这是一个一般意图罪行。如果不是故意,激动中手一挥,即便是打到人眼睛,可能需要赔偿,但不是犯罪。如果故意打人,就构成打人罪了。这个道理也简单,谁都知道打人有害。类似地,像强奸、纵火也是一般意图犯罪 -- 只要是有意干这事,就构成犯罪。
但另外一些罪行却需要具备特定意图 (specific intent)。比如说偷窃。你有意识地拿走一个别人的东西,光有这个事实是不构成偷窃的。构成偷窃必须在拿走别人东西的同时具备永久侵占这个东西的特定意图。
举例说,同学 A 看到同学 B 有一块漂亮的橡皮于是拿回了家,第二天又拿回来还给同学B了。这至少有两种可能。1)A 拿走橡皮的时候只是想借用一下;2)A 拿走橡皮的时候本来是想永久占有这块橡皮(但后来悔悟了)。如果是1)可能有民事责任,但不构成偷窃犯罪。如果是 2),就构成偷窃:A 拿走橡皮的时候同时带着永久占有的目的;至于后来归还不能免除之前已经完成的偷窃罪,顶多是减轻偷窃造成的后果作为量刑的考虑。
具体到华为(美)的员工A.X. 未经允许拿走T-Mobile 的橡皮头测量尺寸是否构成犯罪也完全取决于他的特定意图。如果他只是着急 T-Mobile 的 Tappy 机器人不能正确对华为手机产生触摸反应,想调用华为强大的工程研究能力帮助解决华为手机测试的问题,或者帮助T-Mobile 解决 Tappy 的缺陷(参见前文引用专家分析),这是想做好事,当然不是犯罪意识。如果他是想弄到 T-Mobile 这么高精的绝密尺寸,想让华为偷学美国尖端科技、并想造成 T-Mobile 损失,那可能就是犯罪了。这还只是其个人的问题,要算到公司头上,必须有公司管理层的参与。
根据美国政府起诉华为窃取商业机密 (18 USC 1832)的条款,美国必须证明至少如下四点: 1)所涉及的是商业机密;2)被告目的是给商业机密主人之外的人带来经济利益;3)被告的目的是、或者明知其行为会给秘密的主人带来伤害;4) 被告有意地、未经许可地拿走相关信息。
目前,唯一明确证明了的事情是上面的4)。T-Mobile 对华为(美)的民事诉讼中,陪审团裁决华为的行为不是“蓄意与恶意的”,也就否认了 3)。在接下来的刑事案中,华为(美)很可能防守性启动 issue preclusion简单取胜--民事案低标准都不能证明恶意,刑事案的高标准更不能。反过来,美国政府不能 运进攻性运用 issue preclusion 说民事案确定了华为获取的信息是商业机密 -- 民事案标准低于刑事案。正如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所称,华为在被定罪之前是无罪的。在无罪推定的原则下,被告不需要证明自己无罪,检控方必须证明罪行的所有要素,这是检控方的负担。因此,美国政府必须证明 1)、2)、3),华为罪名才能成立, 而且必须以超越合理质疑的高标准。
美国的起诉书中引用了很多华为的内部邮件,我粗略看了一下,脱离上下文看一段邮件很难直接证明特定意图。华为跟T-MOBILE之间在进行商业合作,遇到测试出现问题,华为手机无法卖出去,肯定得想各种办法。如果你说华为只是为了解决 T-MOBILE 测试华为手机的问题,与这些邮件并无明显矛盾。至于说网传华为给获取 Tappy 信息的人因为获取该信息发了奖金,起诉书中没有这个内容。另外,起诉书不是证据。证据必须符合证据法标准。
3. 华为员工拿走的东西不值钱就无罪吗?
根据美国法律对商业机密的定义,商业机密必须是将其保密可以产生独立经济价值的信息。18 USC § 1839(3)。如果经济价值为零,即使是保密信息也不能构成商业机密,如果无价值信息也就不可能构成窃取商业机密。
前面提到,目前并无证据证明存在犯罪。但即便是华为(美)员工是带着特定犯罪意识窃取了 Tappy 的商业机密,Tappy 的价值大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应该很显然,窃取不值钱的东西与窃取无价之宝存在量刑的差别。美国并未起诉拿走东西的A.X.先生个人,而是起诉了华为公司。公司不是人,不能坐牢, 相关条款规定的处罚是 500万美元以下罚款或者非法获利的三倍 (18 USC 1832 (b))。我没有查阅详细的量刑手册,但可以断定,罚款应该还是跟价值挂钩而不是任意的。如果拿走价值为 $1 的东西却罚款 500万美金,可能违背了 due process 宪法原则。
4. 美国起诉华为是否违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
第五修正案内容很多。网友问的可能是刑事起诉华为是否违反 “double jeopardy”(双重危殆)。双重危殆只适用于同一案件两次刑事起诉。在这里第一个案子是民事案,不存在这个问题。当然,如前所述,华为可能能够运用 collateral estoppel 达到类似的效果。
5. 华为赔偿 T-Mobile 480万美元是什么?
打这个官司,T-MOBILE 索赔上亿美金,双方律师费好几百万美金。取证资料轰轰烈烈数十万页,华为还交出了自己的机器人设计与源代码进行比对。美国陪审团裁定 T-Mobile 因为华为不当获取 Tappy 信息的实际损失为 0 ,华为因为不当获取信息获利为 0。480万是违约损失,具体包括很多理论,包括T-MOBILE寻找替代手机的费用。到底是什么,裁决表上也没有细分。但是,我们可以排除因为 Tappy 信息被获取造成的损失。
6. 华为起诉 T-Mobile 侵犯华为13项专利案子结果如何?
根据美国德克萨斯联邦法院的案卷,华为起诉 T-Mobile 侵犯13项专利。案件双方都提起了总结评判动议,要求不经陪审团审判直接判决自己获胜。T-MOBILE的理由是华为没有及时通告华为拥有这些专利,华为当然提出反对。法官拒绝了双方的动议,双方也就进入准备陪审团审判的阶段。最后双方在2017年底达成协议和解了。和解条件不明。
7. 方舟子说:岳东晓不是律师
世界是变化的。当年美国ABC电视请我以贺梅案法律顾问的身份阐述贺梅案的意义时我不是律师。方舟子依照传票欣然向我提供某新语丝用户IP 地址时我也不是律师。后来我成了美国加州的律师。
【本文原载微博“岳冬晓律师”。】
「赞同、支持、鼓励!」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