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阿藏:未来是富人及其奴隶构成的“智能城市”
凯文·维克托瓦代《馆子》访谈埃里克·阿藏,大卫·布罗德英译,王立秋中译。
(译注:阿藏(éric Hazan),法国作家和编辑,法布里克出版社(les éditions La Fabrique)创始人,着有《巴黎的发明》、《法国大革命人民史》、《街垒的历史》、《1871巴黎公社史》等作品。本文的译注均为中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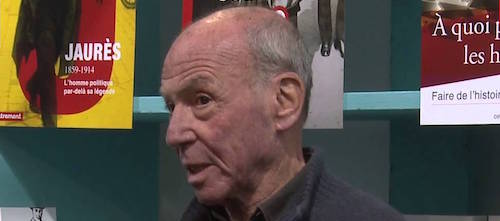
(图为阿藏,图片来源:youtube)
《馆子》:现在,库姆里法案(劳工法)的反对者已经占领巴黎共和广场一个星期了(这次访谈的日期是4月7日)。这场运动也蔓延到了许多市镇和城市。起义,终于是来了么?
阿藏:我不认为这场运动能够带来任何类似于我们现在所想的起义那样的东西。它的目标看起来不过是在法兰西形成一个社会民主力量党罢了——也就是说,它根本不是起义。话虽如此,参加运动的人也有很多不同的立场。但如果你认为巴黎共和广场正在酝酿一场起义的话,我得告诉你,事情并不是那样。
《馆子》:自发的、横向的运动有可能一直持续么,还是说,“先锋党”是绝对必要的。
阿藏:我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扁平式的运动可能持续么?这里所说的“扁平式的运动”这个概念有矛盾的地方。扁平式(运动)的东西肯定会慢慢停下来。我认为在“扁平式的运动”正在进行这个概念里,有异常的地方。不是因为它没有先锋党,现在再也没有人会认为先锋党是必要的了。弗雷德里克·洛尔东在为纵向辩护时,他说的也不是先锋党。显然,我尊重先锋党的观念;我甚至有点崇拜历史的先锋党。但我们不可能一直重复地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广场上的人)同时证明了他们的伟大和他们的失败,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成功地实现了他们的目标。
《馆子》:在《造反的动力机制》(La dynamique de la révolte)中,你指出,“(启蒙)哲人和卢梭破坏了基于神权的君主制的根基,建立了一种新的政治气候”,但是“(法国)大革命却不是为他们所开启的。”在一场反抗运动中,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法布里克有没有通过它的出版物,去实现革命功能的抱负呢?
阿藏:不,出版社不必发挥革命作用。相反,它应该帮着传播各种观念。在人们问我,法布里克出版社的目标是什么的时候,我的回答不是“介入”而是“颠覆”。我们的作用是颠覆既有的秩序——在批评它的方方面面的同时,也致力于让人们知道,(万事除官方的立场外)还有不同的主张。我们必须破坏和建设。至于知识分子的角色,我会问,“知识分子”本身是不是一个有害的概念。这个概念一方面指那些有一定智力的人,另一方面又在暗中区分那些没有智力的人。那什么是非知识分子呢?笨蛋么?傻瓜么?没上过学的人?我不喜欢知识分子这个概念。
《馆子》:甚至在葛兰西的意义上——就知识分子的功能是在社会中传播观念——也不喜欢?
阿藏:无疑,这类人是存在的。但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在即将发生的事情中,我们是不是要把这样的作用专门分配给他们。至于先锋党,我觉得那令人厌烦。我认为它属于过去。
《馆子》:2007年法布里克出版社出版了着名的“隐形委员会”的《来临中的起义》(译注:隐形委员会台湾分部把它译作《革命将至:资本主义崩溃宣言&推翻手册》,并由行人文化实验室于2011年出版)。2014年,你又再次犯忌,出版了该委员会的《致我们的朋友》(隐形委员会台湾分部和行人文化实验室也于2016年出版了它的中译本《致我们的朋友:资本主义反抗宣言》)。这两本书产生的巨大影响有没有让你感到吃惊?你认为他们会有怎样的政治影响?
阿藏:事情分两个阶段。当《来临中的起义》出版的时候,它反响不错,但也没有到供不应求的地步。那本书是2007年春季出来的,到2008年11月,也就是塔纳克事件(译注:指当时九名无政府主义者在塔纳克村被捕的事件,下文所说的朱利安·库帕就是其中之一,被捕原因是因为他们采取了一系列贯彻其理想的直接行动。)爆发的时候,一共卖了7000本。但十八个月就卖了7000本——这对我们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多亏了那次事件,我们现在已经卖出了五、六万本。《致我们的朋友》则得益于隐形委员会通过《来临中的起义》获得的名气。预审法官坚持《来临中的起义》的作者一定是朱利安·库帕。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他所做的整个调查就是建立在整个假设的基础上的。《致我们的朋友》是本非常好的书,但如果没有《来临中的起义》的话,那么它就不会有现在的那种影响力了。
《馆子》:在那本书出版的时候,当时的语境对它来说是不是也很有利呢,考虑到保地者(zadistes)和各种新激进主义(new radicalisms)的出现?
阿藏:是啊,毫无疑问。当时,新的现象确实正在出现。
《馆子》:2006年你写了《LQR:日常宣传》(LQR: la propagande du quotidien),在书中你谴责了语汇的奥威尔化和特定词语在政治和媒体领域中所具备的意义的概率。像“民主”、“共和”、“现代”或“改革”这样的词,在今天还有什么确实的意义么?
阿藏:不,这些词都很灵活。
《馆子》:你会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阿藏:这已经是古老的历史了。甚至布朗基都说过“每个人都叫嚣自己是民主派,贵族们尤其如此。你难道不知道,基佐先生是个民主派吗?”这是一百七十年前的事了!今天,我们在说“自由”的时候,情况也差不多。
《馆子》:但他保卫“共和”,声称“共和就是解放劳动者,就是终结剥削制度。”
阿藏:他也已经在批评那个词。这是老历史了。
《馆子》:你给《地狱天堂》(Paradis infernaux)写过后记,那本书写的是一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代表全球市场中的资本的城市。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语境中,这些新的城市空间是不是在预示着未来的世界呢?
阿藏:那要取决于我们。如果我们任由事情发生的话,那么,当然可能了。也就是说,这种情况是可能的:未来会出现由富人和他们的奴隶构成的智能、互联的“智能城市”,而在这样的城市周围,则是被他们的奴隶放弃的,拱手交给他们的土地。这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噩梦;但要阻止它发生,取决于我们。
《馆子》:你是否理解围绕乌希亚·布特佳(Houria Bouteldja)的《白人、犹太人和我们》(Les Blancs, les Juifs et nous,这本书也是法布里克出版社出的)的争论,很多人——甚至激进的左派,像《一起》(Ensemble)的阿里安娜·佩雷(Les Blancs, les Juifs et nous)——认为那本书有种族主义的嫌疑。
阿藏:布特佳吸引了很多仇恨,这就解释了那本书为什么会引起那样的反应——大多数人读都不读,或者怀着恶意去读。布特佳是个有尊严的人,骄傲的人,在言论和写作中都把自己的观点表达的很清楚。她是个阿拉伯人,还是个女人:对一些人来说,这样的身份太多了。她弄弯了棍子(译注:典出于列宁)。她使每个人都感到厌烦。人们恨她这个人远甚于恨她的某些观念。大部分批评那本书的人都没有读过那本书。我为那本书辩护,而且我为我的言论负全责。
《馆子》:但那本书的书名难道不是已经创造了这样一个负面的假设么?频繁使用像“种族”那样的词和像“我属于我的家庭、我的氏族、我的种族、阿尔及利亚、伊斯兰”这样“惊人”的表述不也适得其反么?
阿藏:她很久之前就已经在解释“种族”这个词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不是一种皮肤的颜色了。怀着善意来阅读的人会理解的。因为一本书用了“种族”这个词就是说它种族主义的人要么白痴要么心怀恶意,要么二者兼而有之。说到底,二者并非不可兼得:你可以是一个心怀恶意的白痴。
大卫·布罗德英译,英译文载:http://www.versobooks.com/blogs/2613-we-have-to-destroy-and-to-build-eric-hazan-on-nuit-debout-the-invisible-committee-la-fabrique-and-houria-bouteldja。 原文标题:"We have to destroy and to build": Eric Hazan on Nuit Debout, the Invisible Committee, La Fabrique, and Houria Bouteldja.王立秋/译。
「赞同、支持、鼓励!」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