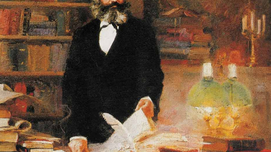深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丰富性及其意义

【提要】马克思着述中成型、定稿的作品很少,留存下来的绝大部分是手稿、笔记、摘录和书信,其观点和体系的丰富内涵并不完全体现在那些表述明确的论断中,而是深藏于对这些观点和体系的探索、论证的过程之中。理论界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所做的许多随意进行阐释,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注重对文本细节的甄别、辨析有关,也导致很难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思想的丰富性和的复杂性。
【关键词】马克思文本细节思想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47(2016)12-0005-05
对于一个思想复杂且产生了巨大历史影响的理论家来说,其观点和体系的丰富内涵并不完全体现在他的那些表述明确的论断中,而是深藏于对这些观点和体系的探索、论证过程中。就马克思而言,尤其是如此。马克思的很多重要思想及其论证,就隐匿于那些散乱的大纲、初稿、过程稿、修正稿和补充材料之中。如果不花大的功夫对其文本细节进行甄别和辨析,而是大而化之、浅尝辄止地对待,乃至满足于外围言说、宏观定性,那么实际上就很难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原初意旨、复杂内涵和思考逻辑;相反,会造成简单化、碎片化、片面化乃至极端化的诠释,甚至严重的误读和曲解。
一、“普遍的个人的解放”,还是“全人类的解放”?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解释为或等同于“全人类解放”,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实践中,“解放全世界”“解放全人类”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口号和梦想。然而,殊不知,这恰恰是马克思曾经竭力深究、撇清的一个观点和思路;因此,很有必要重新甄别一下。
马克思主要是在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中讨论以上思想的。他认为,曾经作为其思想先驱的布鲁诺·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错误就在于:他无视犹太教徒与基督徒的差异,试图用“人(类)的解放”的信念来消弭其分歧。马克思认为,这样的思路和做法“太抽象”了。马克思不仅用世俗关系替代鲍威尔的宗教信念作为观察犹太人问题的视角,用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化解鲍威尔所提出的借助“类”的解放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出路的“抽象性”,而且更深刻地注意到,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其实也只是一个“中介”,较之真正的“人(个体)的解放”,它们也是“抽象的”。
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当然是一大进步,但它还“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还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1]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方面,人通过国家这个中介得到解放,在政治上从某种限制中解放出来。就是在与自身的矛盾中超越这种限制,当然只是以抽象的、有限的、局部的方式超越的。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得到解放的人,仍然只是用间接的方法承认自己,仅仅是通过一个中介(尽管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而使自己得到解放。由此看来,国家只是人和“人的自由”之间的中介者。正像基督是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神性、自己的全部宗教束缚都加在他身上一样,国家也是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非神性、自己的全部人的自由寄托在它身上,仍然不能真正摆脱束缚。
人的自由、发展和解放也是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主将的鲍威尔的旗帜和方向。而在现代社会中,所谓的人权概念、意识和观念更是大行其道,然而只要看看人权的真实形式,就会发现其中大有诡谲和奥妙。
马克思仔细甄别了所谓的“人权”。概而言之,它有两方面的内涵及不同的现实意义:一部分是政治权利,即droits du citoyen,它是与他人共同行使的权利。其内容就是参加共同体,确切地说,就是参加政治共同体、参加国家;它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属于公民权利的范畴。而另一部分是个人权利,即droits de l’homme。与citoyen不同的这个homme究竟是什么人呢?不是别人,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不同于droits du citoyen的droits de l’homme,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就是说,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与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个人的权利。
马克思引用了那部被他称为“最激进的宪法”即1793年《人权和公民宣言》中的论述,指出droits de l’homme是人的自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具体而言,指的是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等等。他特别强调:“这里所说的是人作为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2]就是说,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这一权利就是这种分隔的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可见,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人,正像他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一样,被认为是本来意义上的人,与citoyen不同的homme,因为他是具有感性的、单个的、直接存在的人,而政治人只是抽象的、人为的人,寓意的人,法人。现实的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citoyen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
据此,马克思明确地阐明他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指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3]而政治解放具有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又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而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导致马克思这样煞费苦心的思考没有被忠实理解的原因,一方面与过去中文译本的翻译不无关系。最典型的例子莫如:Niecht die radicale Revolution ist ein utopischer Traum für Deutschland,nicht die allgemein menschliche Emancipation,sondern vielmehr die theilweise,die nur politische Revolution,die Revolution,welche die Pfeiler des Hauses stehen l??t.该句翻译为中文应该是:“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确切地说,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但过去的翻译却是:“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1956、200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3页、第3卷第210页)和1972、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第12页)均是如此,直到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4页)和2012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页)中才得到纠正,但是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不在少数的论者在研读马克思着述时“不求甚解”,并没有深入到马克思的语境、思路和论证逻辑中理解其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发生过变化,但这一观点始终是一直被坚持着的,并被马克思不遗余力地予以强调、深化和推进。诸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哲学的贫困》前“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4]和在该书中更明确提出把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5]的论断;而《共产党宣言》中的名言已经为我们所熟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反复“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那时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认为“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产品”[7]。可以说,这是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始终的中心线索之一。
在马克思思想研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与其基本属于同一时代开始兴起和流行的欧洲非理性主义观念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复杂关系的比较。举凡克尔凯戈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体系而言,可能既是“另类”和“异数”,但又有可以融通和对话之处。在对社会异化、资本操控、人性沦丧等方面的观察、揭露和批判上,他们之间借助“人的解放”议题和关怀完全可以进行深入讨论。
二、准确理解《资本论》对资本的批判
谈及《资本论》,除极少数文献学家外,过去相当多的读者基本上都将其视为一部“俨然已经完成了的着作”,论者也多是借助“成型”的3卷“通行本”来展开研究和阐释。现在看来,这是缺乏真实、完整而权威的文献基础的。随着MEGA2第2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着作”15卷23册出齐,再加上第3部分“书信卷”第8~35卷大量涉及《资本论》的通信和第4部分“笔记卷”第2~9卷作为《资本论》准备材料的4个笔记等文献的发表,马克思准备、写作、修改和整理这一着述的曲折过程被直观而完整地再现出来。同时也表明,《资本论》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手稿群”,其中包括了“笔记”(“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伦敦笔记”和正在编辑的1856—1857年“危机笔记”)、“初稿”(“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和“1863—1867年手稿)、“整理、修改稿”(德文第1卷6个版本;第2、3卷马克思手稿、恩格斯修改过程稿和恩格斯出版稿)和“书信”。
“笔记”是马克思在《资本论》正式写作前的准备材料,记录了他从思想先驱那里汲取思想资源、展开自己的思考和重构的思路及过程,几乎触及到后来《资本论》手稿中的绝大多数材料和议题。特别是由于后来的手稿实际上也非常凌乱,各部分之间的衔接常常出现中断,这些笔记就成为索解马克思复杂的思想结构和叙述逻辑的重要参照。
在过去稍微深入一些的研究中,人们总认为《资本论》有3个手稿,即着名的“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和“1863—1865年手稿”,而MEGA2根据新的文献补充和修正了这种说法,表明所谓《资本论》的“手稿部分”实际上指的就是1844—1867年间马克思所写下的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的所有初稿,而“三个手稿”的说法只具有相对的或特定的意义。
此外,EGA2第2部分为什么甄别《资本论》同一卷次的这些不同版本呢?因为它们之间不仅在字词、段落上有非常多的改动,而且在结构上、内容上也有比较大的差别。用马克思评论第1卷法文版的话说,都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8]。比如,把MEGA2第2部分第11卷(分2个分册)中刊出的《资本论》第2卷的马克思手稿与第12卷刊出的恩格斯对这些手稿所做的整理过程稿以及第13卷刊出的正式出版稿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恩格斯删减和增补的句子、公式和术语以及序列变更等超过5000多处,而且这还不包括标点符号、笔误等技术性的处理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原稿内容的概括部分;有些方面未必“只是形式上的改动”,实际上涉及到对《资本论》思想的“恩格斯式”的理解,而且恩格斯在整理这些手稿的时候,没有查阅过一本马克思当年写作时参考过的书籍。而书信表露了马克思长达40余年艰辛创作的艰难经历和真实心迹,也展示了同道参与这一巨大的思想建构工程的原委和过程。
以上关乎《资本论》的这些材料的刊布,将颠覆人们印象中它几乎是一部已经完成了的着作的传统看法,表明《资本论》“实际上仍然处于一种日益发展的进程中,处于一种没有完成的、开放的,并且是具有疑惑和困境的发展过程中”[9]的实际情形。如果不将这些文献纳入《资本论》研究当中,怎么能不受到极大的局限;又怎么能准确而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的原始思想呢?
更为关键的是《资本论》叙述结构的变迁。《资本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0]。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从来都不是显性地摆在研究者面前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的结构。如何准确、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揭示这一结构及其变动过程,马克思可以说费尽心思。《资本论》理论结构的形成过程,实际就是他的这种探索的忠实记录。由2卷本着作—3本书计划—5个分篇—6册计划—9项内容—2大部分—3卷4册结构—4卷内容的曲折变迁,浸透了一个思想巨匠整整40年的殚精竭虑的探索过程。由于在《资本论》以往研究中,论者的关注点主要对其成型、定稿部分(即恩格斯整理的3卷本)的思想观点的概括和掌握,现在丰富的文献材料的刊布必然要求我们将这种研究转向思想史的探究,转向对马克思曲折的探索历程背后思想视野和嬗变的理解和分析,这将大大拓展、深化《资本论》研究的视野和复杂性。
以上的梳理昭示我们,理解和阐释《资本论》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必须紧扣《资本论》不同版本及其手稿的具体内容;而那种试图从当代重大的现实问题和流行的思潮或者论者自己的观点、思路和逻辑出发去寻找和“挖掘”《资本论》中与其相匹配、关联的概念、表述,似乎这样就可以完成对《资本论》思想的“当代阐释”,这种做法虽最容易和最简单,但也最不可靠。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资本论》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在我看来,对于《资本论》研究而言,“当代”确实是一个特定的视角,以此为基点当然可以“激活”文本中一些过去关注不够乃至被忽略、被遮蔽的思想;然而,如果不注意限度和界域,它又会造成一种新的“片面”,致使另外一些思想被忽略、被遮蔽,时易世变,到那时我们又必须回过头去反复“折腾”文本——这样,不同阶段的研究之间就只有否定、“断裂”而少有传承和积累。
比如说,在冷战时期,人们在对《资本论》的主旨思想进行阐释和概括时特别强调的是:它对“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之本性的揭露和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制度的批判;它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的指导作用;等等。而现在身处全球化时代,很多论者又从中读出:对国家与市场关系和“虚拟资本”的新思考;“存在论”哲学、“生存论”转向与“现代性”内涵;“社会有机体”结构学说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尺度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等等。这样,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思潮的转换,《资本论》研究成为一种“忽左忽右”“可左可右”的随意性言说和“时尚化”追求,而缺少了科学性、客观性和恒定性。这是以往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过的相当惨痛的经验教训。
三、马克思是在什么意义上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从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到1883年去世,马克思的理论创作和实践活动极为耐人寻味。
首先,马克思为《资本论》的整理、修订和扩充持续不断地努力,但始终没有完成定稿工作。这其中既涉及对以往建构的理论体系及其方法、原则的再斟酌;又触及原来关注不够或者没有引起注意的经济现象的分析,诸如金融、银行业和土地制度问题;还有就是70年代之后资本世界的新变化、大量新现象的涌现,使他放弃了“完成”一部成型、完整的着述的工作,而是深入到更为深刻的自我反思、材料积累、视野拓展及其相关复杂问题和现象的探究之中。
其次,马克思意识到自己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突出表现是他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微妙的关系。德国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展览以列表的形式再现了这种关系,即1863年斐迪南·拉萨尔创立“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ADAV);1869年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创立“社会民主工人党”(爱森纳赫派,SDAP);1875年整合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D);1891年起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展览解说词同时指出,马克思对前两个派别组织合并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同意两派的整合;另一方面他又对整合后的纲领很不满意,于是写作了《哥达纲领批判》。但他的意见并没有被接纳和吸收,所以,事实上“马克思生命历程的最后十年,不再专注于政治活动和工人运动,而是致力于历史和人类学的研究”[11]。
第三,马克思发现了自己以往研究不够乃至完全不知的盲区,即对于东方发展道路和由古代向现代转型过程的讨论。为此,他自学了俄语,撰写了大量有关人类学、历史学的笔记,而在他几乎没有自己评论的大量史料的梳理中,原先建构的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得以大大突破:他与基督—犹太传统的关联,与近代人道主义、启蒙思潮和科学理性的瓜葛,他倾心探究但又极为困惑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以隐晦的方式显示出来了。
马克思晚年的努力无疑是他以前的工作的继续。虽然没有写出完整、成型的着述,但无疑蕴含着极大的思想建构的空间和多元实践的路向。更为可贵的是,马克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觉地思考了其学说在未来的命运,当自己的思想苦于在当时已经不能被忠实地理解和转换的时候,马克思发出了沉郁的慨叹:“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2]该如何理解这句振聋发聩的话呢?谨根据我所掌握的文献特做如下的分析,即马克思提醒后继者不能把他的学说理解和演变为作为“超历史”的、“万能钥匙”的“马克思主义”。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谴责了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13],认为“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4]。马克思接着就举了《资本论》中的几处论述来详加分析,指出他本人的学说不是“一把万能钥匙”,不是“一般历史哲学理论”。[15]
笔者认为,为马克思所否认和撇清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指以下三种:
(一)“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流传下来非常明确地披露马克思上述慨叹的文献来自恩格斯1890年的几封书信。在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特别反感把“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当作标签”,只看重马克思主义哲学“依赖于物质存在的条件”而“排斥思想领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把唯物史观解读为“经济决定论”,使“唯物主义”这个词成为“只是一个套语”,“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16]而在8月27日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再次痛斥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设想“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是跳蚤’。”[17]
(二)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马克思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两派之间都声称其主张符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不能协调他们之间的矛盾,但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出,他的学说有被利用的危险。1878年,在给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威廉·白拉克等人的信中,马克思说自己不担心身后其思想被湮没,而是要特别警惕他的学说以后会沦为政党政治斗争的工具和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哲学”,认为那样会“窒息精神创造的本质”,并且举例说黑格尔哲学就是这样衰落的。
(三)垄断思想解释权的马克思主义。同样针对拉萨尔、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展开的纷争,马克思还发出这样的痛心之语:“你们应该明白:把马克思主义垄断化并使它成为一种国家宗教,就意味着卡尔·马克思精神的死亡,而这种精神正是他毕生研究和生活的灵魂之所在。”[18]这里必须强调指出,马克思的这种说法当然有特殊考量和具体语境,所以也不能无限地延伸、引用和肆意发挥,特别是不能用来对当代现实进行评论。但他生前对将其理论和方法做简单化、极端化、“顶峰论”理解的倾向保持高度的警觉并且作出严厉的批评,真正显示了他的高瞻远瞩,也确实发人深省。
注释:
[1]德文原文是“Freistaat”,原义为“共和国”。在这句话中,这个词在字面上也含有“自由国家”的意思。
[2][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第46页;第608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3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7][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第27页。
[9]Carl-Erich Vollgraf:Unsere nicht allt?gliche Editionskonstellation bei den Materialien zum zweiten und dritten Buch des Kapitals.in:MEGA-Studien,2001,S.45.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页。
[11]Museum Karl-Marx-Haus Trier.Karl Marx(1818-1883):Leben-Werk-Wirkung bis zur Gegenwart Ausstellung im Geburtshaus in Trier,2013,S.69-70.
[12][16][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9~603页;第598~599页;第603页。
[13][14][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0页;第730页;第730页。
[18]Museum Karl-Marx-Haus Trier.Karl Marx(1818-1883):Leben-Werk-Wirkung bis zur Gegenwart Ausstellung im Geburtshaus in Trier,2013,S.75。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提要】马克思着述中成型、定稿的作品很少,留存下来的绝大部分是手稿、笔记、摘录和书信,其观点和体系的丰富内涵并不完全体现在那些表述明确的论断中,而是深藏于对这些观点和体系的探索、论证的过程之中。理论界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所做的许多随意进行阐释,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注重对文本细节的甄别、辨析有关,也导致很难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思想的丰富性和的复杂性。
【关键词】马克思文本细节思想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47(2016)12-0005-05
对于一个思想复杂且产生了巨大历史影响的理论家来说,其观点和体系的丰富内涵并不完全体现在他的那些表述明确的论断中,而是深藏于对这些观点和体系的探索、论证过程中。就马克思而言,尤其是如此。马克思的很多重要思想及其论证,就隐匿于那些散乱的大纲、初稿、过程稿、修正稿和补充材料之中。如果不花大的功夫对其文本细节进行甄别和辨析,而是大而化之、浅尝辄止地对待,乃至满足于外围言说、宏观定性,那么实际上就很难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原初意旨、复杂内涵和思考逻辑;相反,会造成简单化、碎片化、片面化乃至极端化的诠释,甚至严重的误读和曲解。
一、“普遍的个人的解放”,还是“全人类的解放”?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解释为或等同于“全人类解放”,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实践中,“解放全世界”“解放全人类”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口号和梦想。然而,殊不知,这恰恰是马克思曾经竭力深究、撇清的一个观点和思路;因此,很有必要重新甄别一下。
马克思主要是在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中讨论以上思想的。他认为,曾经作为其思想先驱的布鲁诺·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错误就在于:他无视犹太教徒与基督徒的差异,试图用“人(类)的解放”的信念来消弭其分歧。马克思认为,这样的思路和做法“太抽象”了。马克思不仅用世俗关系替代鲍威尔的宗教信念作为观察犹太人问题的视角,用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化解鲍威尔所提出的借助“类”的解放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出路的“抽象性”,而且更深刻地注意到,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其实也只是一个“中介”,较之真正的“人(个体)的解放”,它们也是“抽象的”。
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当然是一大进步,但它还“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还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1]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方面,人通过国家这个中介得到解放,在政治上从某种限制中解放出来。就是在与自身的矛盾中超越这种限制,当然只是以抽象的、有限的、局部的方式超越的。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得到解放的人,仍然只是用间接的方法承认自己,仅仅是通过一个中介(尽管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而使自己得到解放。由此看来,国家只是人和“人的自由”之间的中介者。正像基督是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神性、自己的全部宗教束缚都加在他身上一样,国家也是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非神性、自己的全部人的自由寄托在它身上,仍然不能真正摆脱束缚。
人的自由、发展和解放也是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主将的鲍威尔的旗帜和方向。而在现代社会中,所谓的人权概念、意识和观念更是大行其道,然而只要看看人权的真实形式,就会发现其中大有诡谲和奥妙。
马克思仔细甄别了所谓的“人权”。概而言之,它有两方面的内涵及不同的现实意义:一部分是政治权利,即droits du citoyen,它是与他人共同行使的权利。其内容就是参加共同体,确切地说,就是参加政治共同体、参加国家;它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属于公民权利的范畴。而另一部分是个人权利,即droits de l’homme。与citoyen不同的这个homme究竟是什么人呢?不是别人,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不同于droits du citoyen的droits de l’homme,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就是说,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与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个人的权利。
马克思引用了那部被他称为“最激进的宪法”即1793年《人权和公民宣言》中的论述,指出droits de l’homme是人的自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具体而言,指的是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等等。他特别强调:“这里所说的是人作为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2]就是说,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这一权利就是这种分隔的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可见,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人,正像他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一样,被认为是本来意义上的人,与citoyen不同的homme,因为他是具有感性的、单个的、直接存在的人,而政治人只是抽象的、人为的人,寓意的人,法人。现实的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citoyen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
据此,马克思明确地阐明他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指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3]而政治解放具有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又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而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导致马克思这样煞费苦心的思考没有被忠实理解的原因,一方面与过去中文译本的翻译不无关系。最典型的例子莫如:Niecht die radicale Revolution ist ein utopischer Traum für Deutschland,nicht die allgemein menschliche Emancipation,sondern vielmehr die theilweise,die nur politische Revolution,die Revolution,welche die Pfeiler des Hauses stehen l??t.该句翻译为中文应该是:“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确切地说,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但过去的翻译却是:“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1956、200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3页、第3卷第210页)和1972、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第12页)均是如此,直到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4页)和2012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页)中才得到纠正,但是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不在少数的论者在研读马克思着述时“不求甚解”,并没有深入到马克思的语境、思路和论证逻辑中理解其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发生过变化,但这一观点始终是一直被坚持着的,并被马克思不遗余力地予以强调、深化和推进。诸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哲学的贫困》前“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4]和在该书中更明确提出把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5]的论断;而《共产党宣言》中的名言已经为我们所熟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反复“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那时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认为“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产品”[7]。可以说,这是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始终的中心线索之一。
在马克思思想研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与其基本属于同一时代开始兴起和流行的欧洲非理性主义观念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复杂关系的比较。举凡克尔凯戈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体系而言,可能既是“另类”和“异数”,但又有可以融通和对话之处。在对社会异化、资本操控、人性沦丧等方面的观察、揭露和批判上,他们之间借助“人的解放”议题和关怀完全可以进行深入讨论。
二、准确理解《资本论》对资本的批判
谈及《资本论》,除极少数文献学家外,过去相当多的读者基本上都将其视为一部“俨然已经完成了的着作”,论者也多是借助“成型”的3卷“通行本”来展开研究和阐释。现在看来,这是缺乏真实、完整而权威的文献基础的。随着MEGA2第2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着作”15卷23册出齐,再加上第3部分“书信卷”第8~35卷大量涉及《资本论》的通信和第4部分“笔记卷”第2~9卷作为《资本论》准备材料的4个笔记等文献的发表,马克思准备、写作、修改和整理这一着述的曲折过程被直观而完整地再现出来。同时也表明,《资本论》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手稿群”,其中包括了“笔记”(“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伦敦笔记”和正在编辑的1856—1857年“危机笔记”)、“初稿”(“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和“1863—1867年手稿)、“整理、修改稿”(德文第1卷6个版本;第2、3卷马克思手稿、恩格斯修改过程稿和恩格斯出版稿)和“书信”。
“笔记”是马克思在《资本论》正式写作前的准备材料,记录了他从思想先驱那里汲取思想资源、展开自己的思考和重构的思路及过程,几乎触及到后来《资本论》手稿中的绝大多数材料和议题。特别是由于后来的手稿实际上也非常凌乱,各部分之间的衔接常常出现中断,这些笔记就成为索解马克思复杂的思想结构和叙述逻辑的重要参照。
在过去稍微深入一些的研究中,人们总认为《资本论》有3个手稿,即着名的“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和“1863—1865年手稿”,而MEGA2根据新的文献补充和修正了这种说法,表明所谓《资本论》的“手稿部分”实际上指的就是1844—1867年间马克思所写下的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的所有初稿,而“三个手稿”的说法只具有相对的或特定的意义。
此外,EGA2第2部分为什么甄别《资本论》同一卷次的这些不同版本呢?因为它们之间不仅在字词、段落上有非常多的改动,而且在结构上、内容上也有比较大的差别。用马克思评论第1卷法文版的话说,都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8]。比如,把MEGA2第2部分第11卷(分2个分册)中刊出的《资本论》第2卷的马克思手稿与第12卷刊出的恩格斯对这些手稿所做的整理过程稿以及第13卷刊出的正式出版稿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恩格斯删减和增补的句子、公式和术语以及序列变更等超过5000多处,而且这还不包括标点符号、笔误等技术性的处理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原稿内容的概括部分;有些方面未必“只是形式上的改动”,实际上涉及到对《资本论》思想的“恩格斯式”的理解,而且恩格斯在整理这些手稿的时候,没有查阅过一本马克思当年写作时参考过的书籍。而书信表露了马克思长达40余年艰辛创作的艰难经历和真实心迹,也展示了同道参与这一巨大的思想建构工程的原委和过程。
以上关乎《资本论》的这些材料的刊布,将颠覆人们印象中它几乎是一部已经完成了的着作的传统看法,表明《资本论》“实际上仍然处于一种日益发展的进程中,处于一种没有完成的、开放的,并且是具有疑惑和困境的发展过程中”[9]的实际情形。如果不将这些文献纳入《资本论》研究当中,怎么能不受到极大的局限;又怎么能准确而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的原始思想呢?
更为关键的是《资本论》叙述结构的变迁。《资本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0]。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从来都不是显性地摆在研究者面前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的结构。如何准确、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揭示这一结构及其变动过程,马克思可以说费尽心思。《资本论》理论结构的形成过程,实际就是他的这种探索的忠实记录。由2卷本着作—3本书计划—5个分篇—6册计划—9项内容—2大部分—3卷4册结构—4卷内容的曲折变迁,浸透了一个思想巨匠整整40年的殚精竭虑的探索过程。由于在《资本论》以往研究中,论者的关注点主要对其成型、定稿部分(即恩格斯整理的3卷本)的思想观点的概括和掌握,现在丰富的文献材料的刊布必然要求我们将这种研究转向思想史的探究,转向对马克思曲折的探索历程背后思想视野和嬗变的理解和分析,这将大大拓展、深化《资本论》研究的视野和复杂性。
以上的梳理昭示我们,理解和阐释《资本论》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必须紧扣《资本论》不同版本及其手稿的具体内容;而那种试图从当代重大的现实问题和流行的思潮或者论者自己的观点、思路和逻辑出发去寻找和“挖掘”《资本论》中与其相匹配、关联的概念、表述,似乎这样就可以完成对《资本论》思想的“当代阐释”,这种做法虽最容易和最简单,但也最不可靠。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资本论》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在我看来,对于《资本论》研究而言,“当代”确实是一个特定的视角,以此为基点当然可以“激活”文本中一些过去关注不够乃至被忽略、被遮蔽的思想;然而,如果不注意限度和界域,它又会造成一种新的“片面”,致使另外一些思想被忽略、被遮蔽,时易世变,到那时我们又必须回过头去反复“折腾”文本——这样,不同阶段的研究之间就只有否定、“断裂”而少有传承和积累。
比如说,在冷战时期,人们在对《资本论》的主旨思想进行阐释和概括时特别强调的是:它对“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之本性的揭露和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制度的批判;它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的指导作用;等等。而现在身处全球化时代,很多论者又从中读出:对国家与市场关系和“虚拟资本”的新思考;“存在论”哲学、“生存论”转向与“现代性”内涵;“社会有机体”结构学说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尺度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等等。这样,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思潮的转换,《资本论》研究成为一种“忽左忽右”“可左可右”的随意性言说和“时尚化”追求,而缺少了科学性、客观性和恒定性。这是以往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过的相当惨痛的经验教训。
三、马克思是在什么意义上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从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到1883年去世,马克思的理论创作和实践活动极为耐人寻味。
首先,马克思为《资本论》的整理、修订和扩充持续不断地努力,但始终没有完成定稿工作。这其中既涉及对以往建构的理论体系及其方法、原则的再斟酌;又触及原来关注不够或者没有引起注意的经济现象的分析,诸如金融、银行业和土地制度问题;还有就是70年代之后资本世界的新变化、大量新现象的涌现,使他放弃了“完成”一部成型、完整的着述的工作,而是深入到更为深刻的自我反思、材料积累、视野拓展及其相关复杂问题和现象的探究之中。
其次,马克思意识到自己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突出表现是他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微妙的关系。德国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展览以列表的形式再现了这种关系,即1863年斐迪南·拉萨尔创立“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ADAV);1869年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创立“社会民主工人党”(爱森纳赫派,SDAP);1875年整合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D);1891年起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展览解说词同时指出,马克思对前两个派别组织合并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同意两派的整合;另一方面他又对整合后的纲领很不满意,于是写作了《哥达纲领批判》。但他的意见并没有被接纳和吸收,所以,事实上“马克思生命历程的最后十年,不再专注于政治活动和工人运动,而是致力于历史和人类学的研究”[11]。
第三,马克思发现了自己以往研究不够乃至完全不知的盲区,即对于东方发展道路和由古代向现代转型过程的讨论。为此,他自学了俄语,撰写了大量有关人类学、历史学的笔记,而在他几乎没有自己评论的大量史料的梳理中,原先建构的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得以大大突破:他与基督—犹太传统的关联,与近代人道主义、启蒙思潮和科学理性的瓜葛,他倾心探究但又极为困惑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以隐晦的方式显示出来了。
马克思晚年的努力无疑是他以前的工作的继续。虽然没有写出完整、成型的着述,但无疑蕴含着极大的思想建构的空间和多元实践的路向。更为可贵的是,马克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觉地思考了其学说在未来的命运,当自己的思想苦于在当时已经不能被忠实地理解和转换的时候,马克思发出了沉郁的慨叹:“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2]该如何理解这句振聋发聩的话呢?谨根据我所掌握的文献特做如下的分析,即马克思提醒后继者不能把他的学说理解和演变为作为“超历史”的、“万能钥匙”的“马克思主义”。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谴责了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13],认为“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4]。马克思接着就举了《资本论》中的几处论述来详加分析,指出他本人的学说不是“一把万能钥匙”,不是“一般历史哲学理论”。[15]
笔者认为,为马克思所否认和撇清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指以下三种:
(一)“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流传下来非常明确地披露马克思上述慨叹的文献来自恩格斯1890年的几封书信。在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特别反感把“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当作标签”,只看重马克思主义哲学“依赖于物质存在的条件”而“排斥思想领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把唯物史观解读为“经济决定论”,使“唯物主义”这个词成为“只是一个套语”,“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16]而在8月27日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再次痛斥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设想“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是跳蚤’。”[17]
(二)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马克思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两派之间都声称其主张符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不能协调他们之间的矛盾,但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出,他的学说有被利用的危险。1878年,在给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威廉·白拉克等人的信中,马克思说自己不担心身后其思想被湮没,而是要特别警惕他的学说以后会沦为政党政治斗争的工具和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哲学”,认为那样会“窒息精神创造的本质”,并且举例说黑格尔哲学就是这样衰落的。
(三)垄断思想解释权的马克思主义。同样针对拉萨尔、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展开的纷争,马克思还发出这样的痛心之语:“你们应该明白:把马克思主义垄断化并使它成为一种国家宗教,就意味着卡尔·马克思精神的死亡,而这种精神正是他毕生研究和生活的灵魂之所在。”[18]这里必须强调指出,马克思的这种说法当然有特殊考量和具体语境,所以也不能无限地延伸、引用和肆意发挥,特别是不能用来对当代现实进行评论。但他生前对将其理论和方法做简单化、极端化、“顶峰论”理解的倾向保持高度的警觉并且作出严厉的批评,真正显示了他的高瞻远瞩,也确实发人深省。
注释
[1]德文原文是“Freistaat”,原义为“共和国”。在这句话中,这个词在字面上也含有“自由国家”的意思。
[2][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第46页;第608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3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7][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第27页。
[9]Carl-Erich Vollgraf:Unsere nicht allt?gliche Editionskonstellation bei den Materialien zum zweiten und dritten Buch des Kapitals.in:MEGA-Studien,2001,S.45.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页。
[11]Museum Karl-Marx-Haus Trier.Karl Marx(1818-1883):Leben-Werk-Wirkung bis zur Gegenwart Ausstellung im Geburtshaus in Trier,2013,S.69-70.
[12][16][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9~603页;第598~599页;第603页。
[13][14][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0页;第730页;第730页。
[18]Museum Karl-Marx-Haus Trier.Karl Marx(1818-1883):Leben-Werk-Wirkung bis zur Gegenwart Ausstellung im Geburtshaus in Trier,2013,S.75。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赞同、支持、鼓励!」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