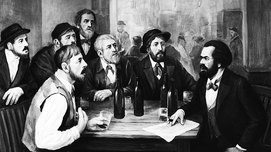安德烈·卡托内: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国际主义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为基础,它推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向社会主义迈进,并不是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本身(从定义来讲,无产阶级仅仅是一个在与资产阶级的辩证关系中才存在的阶级,因此它只有在对资本的依赖与从属状态中才存在),而是为了消灭无产阶级和阶级社会,从而解放整个人类并建立一个具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文化和艺术的人类社会,即恩格斯所说的“自由王国”。就其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是普遍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主义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奋斗的倡议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思想联系。这一倡议曾在多个场合被提及,由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之后又在多个国际会议上得到阐述,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完全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的伟大哲学意义与政治意义,以及它与深藏在工人运动DNA中的国际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普遍主义的理论和政治路径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中表示,中国共产党要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其总的原则。
“命运共同体”这一表述此前也曾出现在各种公开声明和讲话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已经提出了“共同命运”、“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他在谈到台湾时指出:
【】“十三亿大陆同胞和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在这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的不是全人类,而仅仅是中国人民。它指的是一个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大的共同体,但是还没有扩展到整个人类,因此并不具普遍性。
将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指一个比国家更大的共同体[1](例如亚洲或欧洲共同体)扩展到指整个人类共同体,这个质的转变的完成要归功于习近平。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间,“命运共同体”这一表述的使用日益频繁,直到它被写进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的总纲的原则里。
2015年9月28日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以一种清晰而质朴的方式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倡议。通过对这一极其重要的讲话的分析,我们能够捕捉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基本特征,我们也能够确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具有相似或相近意义的其他理念之间的基本差异,例如1950年至1960年期间广泛传播的“和平共处”理念和1985年至1991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领导人期间广泛传播的“相互依存的世界”理念。
二、人类普遍历史与各国人民和工人运动特殊历史之间的关系
作为东方主战场,中国付出了伤亡3500多万人的民族牺牲,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主要兵力……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对历史,我们要心怀敬畏、心怀良知。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塑造。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共同引以为戒。[2]
习近平指出,反法西斯联盟对纳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联合国成立的基础。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以下两点。
(1)命运共同体倡议植根于人类历史,经历了漫长的构思,是反复试错的历史过程以及汲取错误教训的结果。命运共同体不是源自地缘政治而是源自历史。习近平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历史主义,坚持将历史作为生活的导师。
(2)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反法西斯联盟并非偶然。他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判别式和一个主题,一个各国人民可以在其基础上建立他们的未来共同结点,这就是反法西斯主义的判别式。法西斯主义不可成为未来的共同命运。为了构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必须取缔法西斯主义。反对法西斯的斗争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基础,中国人民曾经通过抗日统一战线的斗争为此作出重大贡献。
除了反法西斯主义以外,习近平主席所勾划的命运共同体还确立了以下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3]
这些共同价值如果不融入社会现实,直面其矛盾,它们仍然不过是高高悬挂在天上的美好理想,因为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斥着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世界上,习近平所描绘的共同体还无法实现。因此,必须实现深刻的变革:我们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2008年爆发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4]
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是对盲目地追求自身利益的资本主义的质疑。习近平设想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但却摆脱了侵略性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是一个转型中的世界社会,在那里,公私企业共存,但目的是消除贫困,尊重所有人民的独立性。这是一个非凡的战略规划,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及其所描绘的人类未来。尽管世界还不能立刻过渡到社会主义,但命运共同体理念设想了一个人类再次联合起来的过渡阶段。命运共同体与地缘政治思想截然不同,后者仅关注大国之间的关系(分享世界权力,或者在世界大国之间分配权力)。
许多研究对习近平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倡议的重要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根本指南,是周恩来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续。[5]而万隆会议也是不结盟运动兴起的标志。
一些学者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例如:丁俊和程洪金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中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提出的一个新理念,旨在发展新的国际关系结构,改进全球治理模式。[6]
还有的学者则关注构建一个欧亚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学者、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安德烈·库尔图诺夫(Andrey Kortunov)认为:“虽然中国领导人赋予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普遍意义,但在将其应用于整个国际关系之前,其必须首先关注欧亚大陆的未来。[7]
欧亚大陆无疑对世界的未来具有基础性重要意义,但习近平的倡议超越了欧亚国家边界,它面向的是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地区,即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毫无疑问,命运共同体涉及当今中国这样重要的大国的国际外交,但不限于或也不完全涉及国际关系外交。
命运共同体的范围更为广泛,它已被列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的基本原则,这一事实也确认了这一点。命运共同体向我们揭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内容,它们镌刻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法之中,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和普遍主义在21世纪的当代体现。
从这一角度来看,命运共同体也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启示。按照其中一种解读,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局限于一个严格的民族国家范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仅仅适合中国特定历史的方案,而中国为了本国发展将会把国际主义抛到一边,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发展成为一种民族社会主义。在最恶意的解读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被说成一个用来掩盖完全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道路的意识形态掩护。中国人将成为民族主义者,他们将把马克思的国际主义丢进垃圾箱。这一解读没有考虑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阐述,它们并没有抛弃一般国际工人运动,这个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巨大经济发展和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为了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生产力发展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主要目标),中国遵照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多少年来韬光养晦,集中精力谋发展。但是,在实现基本目标之后,中国便意识到它已进入一个新时代,并再次着重强调马克思普遍主义,以实现人类未来。
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应当认识到,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和把为实现它而奋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战略纲领之一的重大意义。
从这一角度来看,构建新命运共同体理念比国际工人运动历史上出现的其他理念(例如“和平共处”和“相互依存”理念)更具广泛性、更具战略性。
“和平共处”理念具有悠久的历史。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的一些着述中已经提出了这个思想,其目的在于巩固苏维埃国家,承认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永远处于战争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再次提出这个理念,把它当作呼吁西方国家承认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避免核战争的方案。赫鲁晓夫时期,这一方案出现了一些波动,最终美国与苏联签订的一份协议,制止被压迫民族开展争取自由与解放的斗争,因此这个方案似乎是一种静态而非动态的解读,是将两个政治与军事集团之间的形势固定化。和平共处思想秉持将人类划分为对立的系统的理念,因此并没有提出人类联合的目标。出于这一原因,和平共处思想并未考虑不同民族、文化和经济体之间的动态互动。这种理论将世界划分为多个阵营,反对战争,但却无法实现世界的联合。
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新思维”理论中提出了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国民相互依存的主张。然而,在其普遍构想和此后的外交与政治实践中,这一主张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促使苏联单方面裁军并解体。戈尔巴乔夫阐述了相互依存的新愿景,也就是说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而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产生的)情景,它具有如下特征:世界经济关系的国际化;科技革命的全球性;媒体与传播的全新角色;普遍的生态危险;影响到所有人的发展中国家的尖锐社会问题;尤其是因为核武器的出现和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已经危及人类的生存,从而提出了人类生存问题[8]。这些都是证实马克思和列宁所指出的趋势的现实因素:资本的发展已经实现统一并导致世界日益相互依存。然而,戈尔巴乔夫并未强调资本在世界统一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是对这一新情景作了一种中性的描述,结果把谁是决定因素、谁是被决定因素这个谁依赖谁的矛盾(相互依存的矛盾)掩盖起来了:矛盾的两极是平等的,好像你也依赖我、我也依赖你。结果是,例如,我们谈论的不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和依赖它的国家(所谓的世界“南方”),而是依赖“北方”的南方,抑或相反。同样的表述也适用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矛盾:没有雇佣劳动就无法给资本定价,但雇佣劳动与资本根本就不处在相同的条件下,也不承担相同的责任。这种新相互依存理论并没有具体说明矛盾的决定方与被决定方、主要因素与次要因素,在发展过程中失去了辩证法和矛盾范畴。
而习近平的倡议是建立在其他基础上的。这个倡议的阐述也吸收了此前的和平共处与相互依存理念但把它们置于另一个背景之下,因此具有不同的、更广泛的含义和可操作指示。
首先,命运共同体理念中不仅有不同文化存在与动态互动的思想,不同文化彼此相互作用,受到相同的尊重和尊严,都视为人类的财富:我们生活在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中,而所有不同的颜色都为缤纷的世界贡献了一分色彩。
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9]
这可能是一个无法再更好的论述。它使我们超越了和平共处(接受对立制度的存在不一定将导致战争的事实)和相互依存(即遵守相互依存关系)。依存关系——即便是互惠性的,也仍然是一种约束、一种限制、一种消极的关系。在这个论述里,多样性被视为一种财富,它不但不是普遍性的障碍,反而令普遍性更为清晰。“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要实现一个消除所有差异的独特文明,而是把握所有文明的精髓,并在实现人类联合的道路上为所有文明提供支撑。
如果饥饿和苦难继续存在,人类未来是不可能实现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恰恰是通向克服不公正和苦难的一条道路、一个过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提出了拉近文明之间距离的具体提议,这个倡议对于全世界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具有文化价值。“一带一路”和“命运共同体”是旨在实现人类联合的同一条道路上的两个方面。这种统一不可能建立在现存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而必须改变现存的社会生产关系,摧毁最具侵略性的强权,资本主义的动物本能以及对利润的无限渴求。
这个战略倡议涵盖整个历史时代,也可以把它解读为给整个世界制定的一个伟大的新经济政策、一个漫长的过渡阶段,其间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制度、不同的文化与文明为了人类进步而实现共存。从这个战略中可以得出旨在鼓励不同国家生产力发展、尊重并重视其文化的双赢合作协议的理论。
为了将世界转变为一个具有强劲活力与富有前瞻性的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具体而切实可行的道路。它不是一个将当今世界固化的问题: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
命运共同体倡议涉及广泛的领域,是一个从文化与精神等许多方面来观察世界、改造世界的广泛的战略。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指南针,可以指导共产党、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者和进步力量的行动,是消灭剥削、饥饿、苦难和落后的世界统一战线。
注释:
[1]法国学者欧内斯特·勒内(Ernest Renan)19世纪下半叶在关于国家概念的辩论中采用过“命运共同体”的表述。
[2]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全文),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29/c_1116703645.htm。
[3]《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全文),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29/c_1116703645.htm。
[4]《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全文),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29/c_1116703645.htm。
[5]1982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载入中国宪法,宪法规定中国国际关系活动受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约束。
[6]”Ding Jun & Cheng Hongjin:China.s Proposition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the Middle East Governance,Middle Eastern Studies Institut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si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Volume 11, 2017 - Issue 4;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25765949.2017.12023314.
[7]”A.Kortunov,Indo-Pacific or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TUCK MAGAZINE,May 29, 2018; http://tuckmagazine.com/2018/05/29/indo-pacific-community-common-destiny/.
[8]M.C.Горбачёв, Октябрь и перестройка: революци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http://historic.ru/books/item/f00/s00/z0000235/st060.shtml.
[9]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全文),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29/c_1116703645.htm。
【安德烈·卡托内,意大利《二十一世纪马克思》杂志主编。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十二期,授权察网发布】
「赞同、支持、鼓励!」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原标题:【中心刊物】安德烈·卡托内: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国际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