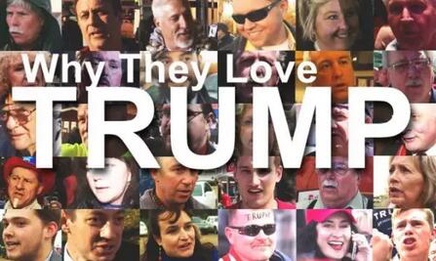作者专栏
-
 洞幽察微
洞幽察微王维佳 | 网络与霸权:信息通讯的地缘政治学
如今的数字网络已经渗透在军事、制造业、农业、金融、零售、物流、城市管理等所有关键的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在主要国家内部,网络化、智能化的信息传播都已经成为发展的引擎。平台经济所构筑的“生态系统”、数据资源所形成的集聚效应、人工智能所预期的科技革命一方面让大型互联网企业成为经济政策的焦点,掌握了大量的公共权力,另一方面却加强了劳动力驱逐,扩大了贫富差距,制造了文化隔膜,在这个意义上,对信息帝国主义的超越,应该同时指向对信息资本主义的超越!
-
 观风察俗
观风察俗理解“后真相时代”的社交媒体恐惧
对于某些西方民主建制派来说,强调当下民众对“真相”的守护固然重要,但是最好不要健忘以往自己篡改“真相”的丑行,否则只会暴露道德表象下赤裸的相对主义。我由此想起整整十年前一个不应被忘记的时刻,2008年的4月19日,柏林、伦敦、巴黎、洛杉矶等世界主要城市的华人举办集会,向全世界发出“支持北京奥运,反对西方媒体片面报道”的声音。“做人不要CNN”,在一片红旗招展的背景中,我依稀记得那响亮的口号。如今,面对“后真相”时代的种种恐慌,人们最终要问:“什么是真相,谁的真相?”
-
 洞幽察微
洞幽察微“软实力”的误区与新的旧世界--从NED说起
中国的海外传播内容主要着力塑造良好中国形象,基本停留在对象认知层面,没有强调任何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的普遍性,其努力的方向仅仅是试图避免对中国形象的负面和不确定性认知。相比之下,塑造价值观认同和制度认同恰恰是美国新闻署和NED这类组织首要且公开的目标。如果以当下全球秩序中的霸权逻辑来理解,中国的海外传播活动不但缺少所谓的“锐气”,反而与中国强大的国际经济影响力反差明显,有些过于“温良恭俭让”。
-
 洞幽察微
洞幽察微细思极恐:反思当代社会的“媒体化政治”
近几年来,“媒体化政治”的现象并没有随着传统媒体的凋敝而消失,反而随着网络媒体的崛起而进一步深化。一批数量众多的媒体化知识分子不断地转移阵地,成为网络舆论场中的主导性力量。相比传统媒体中的专业记者,这些“自媒体人”不再受到机构规制、职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束缚,常常把情绪化的标签、廉价的政治判断和眼球经济的逻辑推向极致。在行政领域,为政绩所迫的公务人员面对网络舆论带来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将公共关系拓展到网络空间。
-
 洞幽察微
洞幽察微忽视劳工大众的声音:美国媒体建制派的失败
从19世纪晚期开始,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大众媒体和职业新闻群体不仅扮演着政治议程的推动者、“客观事实”的呈现者,还一直精心地将自己塑造成社会进步的引领者和普罗大众的代表者。在事业最为辉煌的年代,新闻业的知识精英曾经广受民众爱戴,主流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几乎就等价于西方社会的文化政治共识。而如今,这一切光荣的历史似乎正在烟消云散,新闻界不仅面临产业上逐步萧条的困境,也在感受着历史上少有的孤立和尴尬。
-
 洞幽察微
洞幽察微王维佳 | 危机时代的问题单:谈国际传播秩序的转变
如果要书写一部战后的国际传播历史,那么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就应该是一套全球文化秩序方案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加以实施的历史。建制派媒体是这个国际传播工程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当然还有文化教育领域所涵盖的方方面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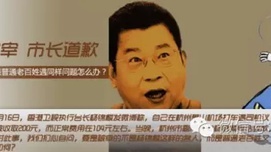 洞幽察微
洞幽察微王维佳:“宣传媒体化”和“行政公关化”--媒介化政治的忧思
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态,有越来越多媒体逻辑和公关逻辑的介入,从危机应对到舆情调查,从国家形象到城市品牌,从政府公关到新闻发布,都是耳熟能详的热词,行政部门日复一日地疲于应付舆论的挑战,给中国的政治生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
 洞幽察微
洞幽察微王维佳: “党管媒体”理念的历史生成与现实挑战
通行了几十年的市场化、产业化发展路径已经让大众传播业的性质发生了转变。无论是“党媒”还是其他类型的媒体,都渗透了大量商业化和资本化的元素,产业属性自然包含着逐利性的本质。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国历史中最倚重的群体,逐渐成为被包括党媒在内的大众媒体忽视和抛弃的群体,这自然是媒体市场化改革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
-
 洞幽察微
洞幽察微“媒主”政治--利益集团绑架政治的工具
媒体市场化规定了商业媒体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只有那些在市场中占据优势的政治力量才能依靠市场机制与商业媒体形成同盟关系。国家把媒体的控制权拱手让给市场中占据主导的政治力量,让他们运用市场模式下培训成熟的人才队伍,去塑造与公共治理目标相互对抗的文化政治,这种政策思路的蹩脚之处是十分明显的,它的政治后果甚至也是可以预见的。
-
 洞幽察微
洞幽察微美国政府是怎样输出价值观的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逐渐把向世界传播、输出美国价值观作为巩固其全球霸主地位的重要手段。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将文化价值观输出和意识形态安全放在了更加突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