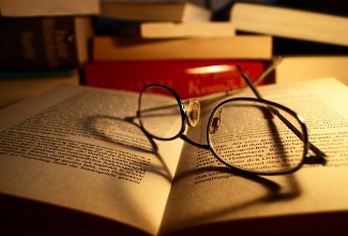圣诞快乐还是节日快乐?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www.cwzg.cn的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保留本声明。】

微信群和公众号里有人开始发“平安夜”的歌曲了,哦,又是一年要过去了。
每逢圣诞中国这边节日气氛也是特别浓厚,街上随处都是圣诞装饰,走哪儿都漂着圣诞歌曲,Eve那天晚上有些城市凡能挤人的空间人头攒动都被挤得爆满。圣诞是基督耶稣降生的日子,在西方是宗教盛典,而在我们东方,人们这么起劲地过圣诞节纯粹是寻乐子瞎凑热闹。日本人第一个想到把圣诞节变成圈钱的商机,于是一到Eve单身们就会发愁,他们都不好意思跟人说自己一个人独守了圣诞夜 ,日本商人把这个宗教节日成功打造成了东方的情人盛会。现在这股风吹到了中国,中国商人对钱的贪欲丝毫不输日本人,有钱不赚那是那啥,因此说中国人过圣诞是瞎凑热闹这话失之片面了, 商人们的目的是很明确的。
我从来没有以凑热闹的心态看圣诞,我是一直把它视为宗教性质的活动的。我对圣诞节最初的记忆来自幼儿园,那时我在上海,记得是看演出,第一次知道了圣诞夜扛着袜子做的口袋给小朋友们送礼物的圣诞老人。上海嘛外来文化的影响比中国其他地方要早一点的。
第二次关于圣诞节的记忆比较震撼,也就比较入心。那是八十年代第一个年头,我在大学。一个朋友的朋友是基督教徒,那年圣诞夜我出于好奇,求那个朋友 带我去缸瓦市的教堂,在那里观摩了圣诞弥撒,第一次听到唱诗班唱的圣歌。我是无神论者,自信不会被任何宗教打动,但那个场面还是让我感到了一种神圣庄严的气氛。震撼我的并不是圣诞弥撒的仪式,而是那位基督徒朋友的遭遇和经历。
基督徒朋友是一个漂亮聪明的姑娘,却不幸有家族病史的遗传,她是个精神病人。她母亲早亡,从小被父亲一手拉扯大。父亲是混血,有一半德国血统,因此文革中被诬陷为德国间谍吃了不少苦头。许是这样的经历激活了体内的遗传基因,他父亲犯病了,不久她也跟着犯病了。为了减轻痛苦,为了抑制狂躁保持内心的平和,也是为了在精神上支撑下去,他父亲把她带进了教堂,从那以后她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当我看到她面向她的上帝时那双清澄的眼睛,我懂得了对一种宗教的尊重。
但有例外,也有不安。一个曾经的朋友,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说是佛教徒是因为她总说她自己是离佛最近的人,说她经常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佛光,可以看到佛光照耀下佛祖的降临,有时候半夜里醒来朦胧中会看到佛就在她面前,她会和佛对话。我因为尊重宗教,所以从不反驳她,更不会拿她取笑,相反对她有点敬畏。但突然有一天她对我说,她被一个朋友拉去参加了一个基督教的活动,并说她的那个朋友有意拉她入教,我提醒她不要忘了自己是离佛最近的人,对别人的劝诱一定要慎重。再过了一些日子,我们Q聊,谈及当时发生在日本的大海啸时她充满爱意地祈祷主保佑所有的生灵,她用“阿门”结句时我仿佛看到她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我愕然!不是愕然她的变节,而是惊奇她从“我佛慈悲”向“愿主保佑”的转换,原来是这样的自然,这样的简单,不需要羞羞答答,于我听来也没有丝毫的违和感!和谐、博爱是所有宗教共通的吧?不管怎样,从此我和她失去了联系。
我新近在远离北京市区的山脚下选择了一块栖身之地,这里很荒僻,荒僻到如果我的同龄人初来这里,一定会有回到插队时代的时空错觉。附近看上去没有太多的人迹,镇子上没有大型商铺,没有像样的饭馆,倘若偶尔有坐在比如咖啡馆那样的场所小资一下的冲动,还是想都不要想的好。但让我吃惊的是,这里有教堂! 我不知道那能不能算是教堂,没有尖尖的房顶,没有十字架,只是一个稍大的普通农屋,透过玻璃窗看得见里面摆着好几排长凳,墙上挂着十字架,门口有某某教会字样的牌子。出入教堂的信徒基本都是外地口音,是来北京务工谋生活的一群。有一天我从教堂附近路过,从教堂里传出一群人合唱音阶和 琶音的声音,是练习,一定是为圣歌在做准备,声音整齐、热烈、认真。我边走边听边想,我们这块从来没有基督教生长基础的土地什么时候冒出来这许多笃信上帝的信徒?外来宗教都渗透到如此偏远的山脚之下,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搭错了哪根神经?宗教的力量太可怕,它能把一群毫无组织、互不相识的乌合之众捏合在一起,让他们规规矩矩地对一个外国的神表现出虔诚。我们当地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是否尝试过把外来人群组织起来开展一些健康的活动,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和能力吗?老实说,拿到过去应该有,现在没有!我尊重宗教,我不干涉别人信教,但我感到不安。
和圣诞节的第三次接触是1987年。那是临近圣诞节的某一天,我们部吴导拿来一盘录像带,那是美国人制作的一部动物世界欢度圣诞节的卡通片,里面的角色诙谐可爱,按照现在的流行说法,萌得不要不要的,而且故事感人至深。大家看完后吴导提议把这部片子译制出来,赶在圣诞夜播出,重点是不外请演员,剧中所有角色的配音由我们工作人员自己来完成。吴导的建议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就连一向注重政治把关的部主任也跟着大家热议起来,没表示反对。说干就干,只一天功夫制作完成,手到擒来的事儿嘛。一想到圣诞夜要播出我们自己配音制作的节目,大家还是有点小激动的。不料圣诞前夜的前夜那一天,主任满脸严肃地宣布上级通知,我们那个卡通片被取消了,理由是该片宣传宗教不宜播放。主任是秉公办事,没毛病,但我们在底下议论开了,大家觉得没必要上纲上线把一部卡通片和宗教联系起来,对那种夸张的过敏反应众口一辞表示非常地不服。
时间过得太快,那都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三十年啊!那时我们不服,但三十年后的今天,我服了,真的服。
记得是进入千禧年后的某一年,我在圣诞前夜的那天下午赶到加拿大的维多利亚。难得的机会,我提出想直入当地人的生活,和他们一起体验一个真正的、地地道道的圣诞夜。我期待着在当地人家温暖的壁炉前,在圣诞树彩灯的闪烁中大快朵颐流着肥油的烤鹅……我想像着那座与西雅图隔海相望的小岛灯火通明、人来熙攘的热闹景象……然而,迎接我的是一座死城,一座几乎看不到车辆、看不到灯光、看不到行人、看不到餐馆商店的死城。我的住处有圣诞树,有彩灯,有壁炉,但没有烤鹅!说好的圣诞夜呢?
简单晚饭后他们把我带到了一座教堂,那 里像是一座大剧院,有两层观众席,黑压压挤满了人,仿佛岛上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了那里,难怪大街上一片死寂。我们去晚了只能站在舞台一侧的上方,从上斜着往下看就是神父的侧背。然后圣诞弥撒开始了,全体起立跟着唱诗班一起引吭高歌。人们人手一本歌谱,我手里也被塞了一本,难以置信他们要把歌谱 里的歌全都唱一遍?干干地站在那里即累又无聊,干脆我也扯开嗓子跟着众人一起唱了起来,我想麻痹自己忘记疲劳,不过确实也挺乐呵。第二天同行的日本姑娘美纪把她的日记拿给我看,她是这样记述那个圣诞夜的:没完没了地唱歌,冗长的宗教仪式,今年的圣诞节过得索然无味……她对我能够滥竽充数跟着众人一直唱到最后感到吃惊,在日记里狠狠赞了我一把。
这就是我经历的一次欧美人真正的、地地道道的圣诞之夜,没有美食,没有狂欢,没有烟火礼花,只有一场肃穆但却疯狂的宗教仪式。当我见识了,才知道自己以前的浅薄,真正的圣诞节是不能从宗教中剥离出去的。
今天,每逢圣诞,我们从众地互道一声“Merry Christmas”以示庆贺,一般不会去追究Christmas这个词的构成和原意。其实Christ就是基督,后缀mas就是宗教节日祭奠的意思,可见即使从词源的角度,把圣诞节与宗教剥离也是错误的。
有人说“圣诞节”翻译得有问题,将基督之诞生谓之圣诞是崇洋媚外的表现。我仔细琢磨了一下,倒是觉得把“christmas”翻成圣诞,实在是精妙之笔,独具匠心。一个“圣”字点出了基督教在欧美独一无二的至上地位,道出了欧美诸国喜欢强加于人的文化优越感。当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随着世界多极以及多元社会的形成,欧美人的那种文化优越感已经日渐式微,世界正在发生变化。
近些年,尊重个人信仰、不将信仰强加于人已成为欧美社会的政治正确,因为圣诞节的特定宗教性质,越来越多的非基督徒、无神论者、甚至一些坚持政治正确的基督徒开始抵制“Merry Christmas”,代之以“Happy Holiday”来互道节日的问候,一个去宗教化圣诞节的政治时尚正在悄然形成。
2015年美国国内的星巴克因杯子上印有圣诞图案而遭到非议,据说从那时候起星巴克的杯子再也见不到圣诞树和圣诞老人的踪迹了,代替它们的是热烈的大红一色。
不仅星巴克那样的商家,即便是美国总统面对政治正确也同样不落俗套 ,比如小布什和奥巴马,他们心里装的只有选民及其爱好,圣诞来临时他们一定要把“Happy Holiday”和“Merry Christmas”的祝词同时献上的,两边讨好,才能两边通吃。
只有特朗普例外,这个愣头青老右派上台前就许下诺言,发誓圣诞之际决不做机会主义者,他只对美国人民说 “Merry Christmas”。这个说到做到的疯老头让狂热保守的基督徒们在平安夜着着实实激动了一个晚上。其实我也比较喜欢特朗普的表里如一,本来嘛,宗教就是宗教,装什么装!
不过潮流毕竟是潮流,不会因为特朗普怎么样就会改变它的势头和方向,今后在西方越来越多的人在过圣诞节时会用“节日快乐”(Happy Holiday)代替“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看来这是趋势,这种趋势总有一天也会迫近我们东方,而碰巧如果赶上你也正想追时尚凑热闹体验一把圣诞节,你就有可能不得不在“圣诞快乐”和“节日快乐”之间做出选择,到那时你选哪个呢?
「赞同、支持、鼓励!」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cwzg.cn/politics/201811/455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