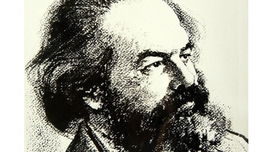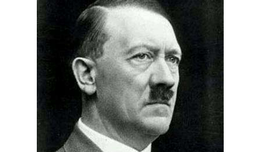思潮辨析:历史假设的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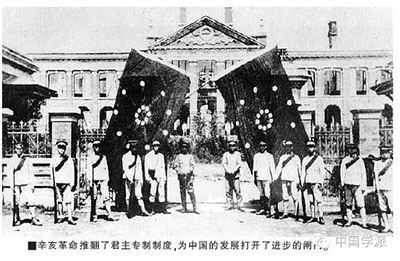
学术主持:
彭秋归(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编辑)
对谈嘉宾:
林 剑(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苏全有(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李永胜(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1、历史假设应符合逻辑和常识
假设应当是对具有偶然性的事件提出假设,即对有可能这样发生,也有可能那样发生的事情进行假设,并且应当有正确的世界观作指导。
彭秋归:在历史研究中,假设是一种颇具争议的研究方法。建立在充分历史可能性上的严肃假设,从多元视角展现了历史研究对于现实的资鉴意义,无疑具有一定正面价值。然而,假设也有边界,需要加以限制。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界定真正意义的历史假设?
林剑: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以降的历史学家一直坚守的史学求真的传统,西方史学界产生了一股反叛思潮,提出了一些创新史学研究与诠释的新方法,形成了一股被称为“新史学”的潮流,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种便是“假设史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无疑受到自然科学研究中假设方法的影响与启迪,作为一种史学研究与诠释的方法本来无可非议,如将历史研究视为一种科学的话,是可以合理借用和采用在其他科学研究中被证明有效的假设方法的。然而,在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过程中,一些人片面地对假设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进行了不加限制的无限夸大,凭自己的主观臆断对历史任意地进行假设与推断,因而受到了不少人的质疑,甚至于日渐式微。
近年来,被称为“假设史学”的史学观在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其风似有越刮越盛之虑。“假设史学”认为历史是人们选择的结果,假设人们的选择不同,历史的趋势性结果就可能不是唯一的,而是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因此,“假设史学”认为在历史研究中可以有不同的假设,并以多种不同的假设为基础得出多种不同的“假设性结论”。一些对假设方法在历史研究与诠释中的作用任意夸大的史学观或史学思潮,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忧虑,更应引起我们的必要警惕。
苏全有:在我看来,历史发展大的方面,宏观而论,有固定的发展方向,具体而微之,则具有多歧性。因此,假设要落脚在具有多歧性的方面,而非其他。
历史发展分为有可能的发展趋向和不可能的发展趋向,可能性是进行假设的前提。比如袁世凯称帝问题,假设袁世凯不称帝就是伪命题,是不成立的假设。梳理袁世凯的人生之路可知,他有非常浓郁的传统帝王思想,一心一意想当皇帝,此乃其人生的不二诉求,而且他急于当皇帝,且自信能当上皇帝,加上袁克定的太子梦以及杨度、梁士诒等人的助纣为虐,可以认定,袁世凯称帝乃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第二种可能性。因此,假设袁世凯没有复辟帝制,没有意义。事实上,此类假设不仅没有意义,而且还有害。其所造成的无意义论争,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使得历史研究表面看热闹非凡,实则喧嚣的背后是沉寂。
李永胜:谈到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需要对历史假设的具体含义进行界定。已经发生的客观历史过程,没法改变,也不能假设。但是,人们评说历史总是喜欢提出一些假设的命题,表述自己的历史见解。假设历史是历史研究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方法,比如,毛泽东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这其实就提出了一个假设命题。人们在表述历史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使用假设命题。提出历史假设应当符合逻辑和常识。假设应当是对具有偶然性的事件提出假设,即对有可能这样发生,也有可能那样发生的事情进行假设,并且应当有正确的世界观作指导。
2、主体能动性与选择性不能无限放大
人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并不是一种纯主观性的活动,而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统一,或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人的生命活动的双重性质决定了人的实践活动的自由性质,同时也决定了这种自由的定在性、非任意性与历史性。
彭秋归:谈到历史的可能性与偶然性,我们知道,历史假设是在历史的无数力的总的合力中,假设某一种“力”发生变化,从而造成全局的改变。这种假设强调个人的作用,强调历史的偶然性,这就涉及我们如何看待历史人物或者偶然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林剑:在我看来,历史不能任意假设,不能任意夸大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在个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任何单向度的思维方式无疑都是错误的,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我们不否定历史人物对社会历史的影响作用,这是我们对人类历史上的英雄给予褒奖、对阻碍历史进步的人给予贬斥的根据与理由,但我们更应加以强调的是,所有的历史人物,正面的历史人物也好,反面的历史人物也好,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是历史的时势造就出历史人物,个人对历史的作用与影响及其作用与影响的方向,既取决于他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实际地位,也取决于他对历史必然性的把握与遵循。
历史不能任意假设,不能过度夸大人的主体能动性与选择性。一些历史假设不仅夸大了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同时也夸大了人作为人存在所具有的主体能动性与选择性的作用。他们通常打着反对历史预成论与历史宿命论的旗号,将人的主体能动性与选择性无限放大,在他们的理论逻辑中,历史不过是人们选择的结果,如果人们有着不同的历史选择,无疑便会有不同的历史结果。历史不是预成的,而是生成的。在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逻辑中,决定论原则虽然是一个核心性原则,但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历史决定论并不是一种神秘的预成论或宿命论,它不仅不拒斥人的选择的可能性,反而始终将社会与历史视作在自己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生成的存在物,视作人的社会与人的历史。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规律的生成都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并且随着人的实践活动的发展而演进。历史是社会的历史,也是人的历史,“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人的劳动发展史是全部社会发展史的基础,也是理解全部社会发展史奥秘的一把钥匙。实际上,当马克思的历史观将人视作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与主体,将人的实践、劳动视作整个社会历史生成与发展的基础时,在理论的逻辑上也就蕴含着对人的主体能动性与选择性的肯认。但是,人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并不是一种纯主观性的活动,而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统一,或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人的生命活动的双重性质决定了人的实践活动的自由性质,同时也决定了这种自由的定在性、非任意性与历史性。相对于社会历史来说,人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其活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前提、基础与条件的规定与限制,对于每一个特定阶段的人们来说,他们只能做或完成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所允许做并有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不可能做客观条件不允许做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任何人即使是那些被视为“天才”或英雄的人们,其行为的选择也不能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的限制与允许,逾越了这种限制与允许的雷池,就要承担失败的后果,受到历史的制裁。
李永胜:唯物史观认为,历史发展有规律性。在个人与历史发展关系上,认为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个人对历史的影响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的要求和限制。历史发展有其规律和必然性,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但是某些历史假设命题否认历史必然性,而认为历史过程是偶然发生的,并且往往夸大个人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和作用。
就以慈禧太后、袁世凯对清室退位的影响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传甚广的“告别革命”论提出一种假设:如果武昌起义时慈禧在世,袁世凯不敢心存异想,清朝不会亡。这样,中国就会形成以清朝皇帝为首的君主立宪制,并长期延续下去。这种观点把清朝灭亡的因素看得过于简单了,清朝灭亡绝非一个袁世凯心存异想的问题,促成清朝灭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满清统治者入关建立全国性统治,这种统治是建立在军事力量威慑基础上的,但二百多年后,旗兵早就失去了战斗能力。相反,汉族人的军队已相当大程度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武昌起义就是清政府编练的新军发动的起义,袁世凯的北洋军队也并不忠于清朝。没有一支可靠的军队,清朝统治靠谁来维护?革命派以推翻清朝为己任;立宪派指望清廷真正立宪,但清政府却搞假立宪,导致立宪派失望,不再支持清政府;清政府的部分地方督抚和朝廷官员,对清政府也不再拥护。武昌起义爆发,各地革命党人、督抚、清军军官纷纷响应,许多清朝官员摇身一变为革命政府的首领。可以说,革命派、立宪派、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官僚派合力促成了清帝的下台,并非袁世凯一个人决定了清帝的去留。
袁世凯是否心存妄想,决定的因素并不在于慈禧是否在世,而是清朝统治力量的强弱。如果清政府分崩离析,无法控制局面,即使慈禧在世,袁世凯照样会心存妄想。不可否认,袁世凯要挟清帝退位,是清亡的原因之一,但是没有武昌起义,没有全国各地纷起响应反清革命,清廷根本无须重新起用袁世凯,袁世凯也就不存在逼退清帝的问题了。南北和谈过程中,没有南方革命党人的压力,袁世凯也没有理由要求清帝退位。到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已经统治不下去了。
清朝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绝非偶然,慈禧太后、袁世凯个人无法改变这一历史趋势。
3、建立在不真实的认知之上的“自由”没有生命力
学术研究固然要打破禁忌,打破框框,放飞心灵,自由飞翔,但决不可以有悖于历史发展规律。建立在不真实的认知之上的“自由”,没有生命力,也没有价值,仿如沙滩上的大厦,再美丽,也是要倒塌的。
彭秋归:说到慈禧、袁世凯的问题,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上的假设,总是容易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比如,革命不如改良,假设按照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由清政府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度,中国就能避免因革命造成的巨大动荡与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等,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李永胜:“告别革命”论者称,清末的戊戌变法和预备立宪都有成功的可能。如果成功,中国将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根本无须革命;如果慈禧早死十年,光绪亲政,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就成功了;清廷预备立宪并非虚假立宪,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很有可能取得成功。这些假设过于夸大了个人对历史的作用。不论是慈禧还是光绪,他们都是深居皇宫的统治者,其政治立场没有本质差别。他们都必须顺应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进行某些改革。事实上,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很多政策是一脉相承的。戊戌政变期间的帝后矛盾主要源于权力之争,并非政见之争。慈禧和光绪,不懂得君主立宪制的真正含义,他们也不会赞成君主立宪,将自己的权力拱手让人。纵观欧美各国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的转变过程,经历了长期的动荡和曲折,哪能几年时间就完成这一转变呢?
“告别革命”论者还有一个重要论点是,辛亥革命开启了以后几十年的不断革命,延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如果保留清政府,就不会有军阀混战局面出现。这种假设不合情理。时代总要进步,清政府被推翻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推翻清朝统治后,中国出现一定时期的乱局,这是难以避免的,是革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世界上许多国家革命之后都经历了长期的动荡局面才得以安定下来。
“告别革命”论者,自称不否定革命,只是主张“告别革命”,声称革命也有好的一面,即带来了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但又说辛亥革命只具有思想史的意义。说革命带来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如果说革命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就不对了。革命不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而且实实在在为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就辛亥革命而言,尽管其不彻底,但是毕竟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将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林剑:康梁变法的失败,深刻的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不同于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国际国内的客观条件与时势已不允许中国像日本一样走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道路。不仅外部的列强不允许中国变强,统治阶级的内部不允许变法维新,人民群众也不愿意再接受一个腐朽的封建制度与封建王朝。康梁变法失败之后,改良主义思潮陷入式微,维新之路被国民抛弃,革命虽屡遭挫折与失败,但革命的浪潮却一浪高过一浪,不仅革命成为世纪的主题,而且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些历史的转折,是由客观的历史条件使然,是国内外的各种矛盾的交汇与各种历史条件决定了当时的中国走不通维新改良的道路,同样也是国内外的各种矛盾交汇与各种历史条件决定了革命成为了一种必然性的选择。
现在,有些人基于另外一种史学观,在史学研究的多个领域中,尤其是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中,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设。在这些假设中,要么夸大某些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要么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事变诉诸人为的纯粹偶然性的解释,试图从中推论出一些有别于既成事实或者实然状态的另一种发展道路与另一种历史结局的可能。这种假设应该引起我们的必要警惕,因为在思想上它会颠覆人们对唯物主义历史观所坚持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规律性思想的认知,颠覆人们对中国革命的逻辑与革命史的正确认知,在政治上动摇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革命道路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信念与信心,它想诱使人们,并有可能诱使人们相信,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制度并非唯一与正确的选择。
苏全有:我们很容易就关注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的假设。其实,古代史也有假设研究,比如关于诸葛孔明北伐中原问题,大汉情结之下,有人出于对其中的偶然性抱有千古遗恨,从而不自觉地假设。古代史如此,类推之于世界历史,亦如此。因此,和近现代史一样,假设研究在古代史、世界史领域都有一定的存在。至于其中的不同之处在于,近现代史领域的假设研究多对当下具有负面的政治影响。比如有人称,假设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假设慈禧成功实行君主立宪,假设袁世凯没有复辟帝制等,这一类的假设,如若认定为成立,则20世纪中国的发展道路将是资本主义道路,而非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且为国人所选择了的社会主义道路。
学术研究固然要打破禁忌,打破框框,放飞心灵,自由飞翔,但决不可以有悖于历史发展规律。建立在不真实的认知之上的“自由”,没有生命力,也没有价值,仿如沙滩上的大厦,再美丽,也是要倒塌的。
4、不反对假设方法 但反对“假设史学”
社会历史有其自身的规律,在历史偶然性的背后,隐藏着历史的必然性,这种规律性或必然性的存在,既为人的主体能动性与选择性提供着可能性空间,也为人们的自由的任意性设置着障碍与限制。
彭秋归: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对于历史假设方法来说,有人用它来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有人用它来否定历史发展的规律。如何对待历史假设,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苏全有:唯物史观在假设研究方法运用上的指导作用,就是要强调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在符合历史可能性的前提之下,进行可行性的阐释,从而得出科学、客观的结论,进而推动史学研究走向深入。因此,历史研究并不排斥假设,因为假设确实可以开阔研究者的视野,开拓新视域,让科学的历史研究中泛起哲学玄思的涟漪。
我们不反对假设方法,但反对编造历史的“假设史学”。假设运用到史学研究当中,一定要客观、全面,摈弃个人的主观预设,需要强调的是,大胆的假设要以小心的求证为前提。当今学术界有的研究者在假设问题上,大胆有余,小心求证不足,甚至是无心求证。
林剑:历史之所以是不能任意假设的,不能对历史人物,乃至于整个人类创造历史的能动性与历史选择性进行片面性的膨胀与夸大,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一样,是一种有规律的发展与演进。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既不同于形形色色的预成论或宿命论,也不同于形形色色的非历史决定论。非历史决定论从根本上说否定客观规律的存在,至多也仅限于对自然规律的承认,而对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是否存在客观规律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持拒斥态度的。唯物主义哲学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是一种决定论,更为重要的还是一种彻底决定论。所谓彻底是指它将决定论原则贯彻于它的哲学的所有领域,即不仅贯彻于自然界的领域,也贯彻于社会历史领域。
在唯物主义哲学视野中,不仅自然界的运动是有规律的,社会历史的运动同样是有规律的。关于社会历史的规律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系列的经典着作中,曾有大量的、详尽的、明确和不容有疑的论述,无须一一加以引述。需要强调的只是,其一,社会历史规律较之于自然规律,虽然在生成方式与表现方式上各有不同特点,但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同自然界的发展一样,也表现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社会历史中存在的规律也是一种“自然规律”。其二,社会历史规律人们是可以认识与利用的,这种认识与利用“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即可以加速历史的进程与减轻历史发展的代价,却不可人为地跳过或用法令取消它。
对于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说,所谓的“假设史学”是不可接受的,之所以是不可接受的,深刻的理由是社会历史并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女孩。社会历史有其自身的规律,在历史偶然性的背后,隐藏着历史的必然性,这种规律性或必然性的存在,既为人的主体能动性与选择性提供着可能性空间,也为人们的自由的任意性设置着障碍与限制。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所谓的“假设史学”是不可接受的,接受了这种“假设史学”,无疑会导致我们信仰堤坝的崩溃,因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奠定在历史规律与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之上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所谓的“假设史学”是不应接受的,否则就会使我们对自己的历史认同感与所走道路的信心产生动摇。
「赞同、支持、鼓励!」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