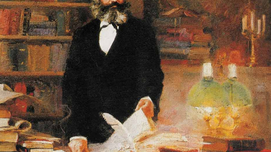书斋里的史博德先生和他的马克思

史博德先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的思想转变”。而中国的记者则如获至宝,马上大笔墨渲染这个“转变”。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我们,却有必要认识这个“转变”,了解这个“转变”,从而分清楚这个“转变”究竟是什么,意味着什么。
说马克思的前后断裂,用青年马克思的观点去反对成年马克思的观点,这并不是史博德先生的发明,这是“学者”先生们早就掀起的论争。在欧洲的学者先生们那里,这种“转变”有一个更加动听的名字:“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史博德先生的博士论文也在这个论争当中搀了一脚。那就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场论争吧:这场论争早在1931年就开始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各种各样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哲学家们、宗教家们都蹦了出来,与史博德先生相反,他们肯定的是青年马克思,他们宣称,青年马克思就已经完成了他的哲学发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都已然成形。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资本论》中体现的哲学方法,则是对青年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背叛”。所以,要得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就要回到青年马克思主义去,也就是说,要用一种“人道主义”的批判,来代替具体的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于是,他们转向了文献的研究,他们要去研究,马克思在什么时候成为了一个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在什么时候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这些学究们汲汲于为这些问题找到一个“精准”的答案,歌德笔下的德国教授大概指的就是这些学者们。我们的史博德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德国教授,他可以骄傲地宣称,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了解马克思的手稿,他从手稿出发,用成年马克思反对青年马克思,用一种“思维游戏”,一种有趣的“哲思”,来反对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史博德先生宣称,这种“思维游戏”,才是马克思的思想精髓,我们的德国教授在自己头脑里构造了一种玄之又玄的结构:经济的发展自然会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私有制的发展自然会导致对私有制的否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不要人为的“干预”,更不要什么政治革命,终究有一天,私有制就会自动地结出否定私有制的果实。于是乎,《财经》杂志的蹩脚记者与着名的德国教授在谈笑间便把马克思塑造成了一个鬼才,晚年的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原来可以和平长入到一个更高、更美好的历史阶段,就像下雨之后蘑菇自然而然就长出来一样。在史博德先生看来,那些成天嚷着要搞政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仅仅是一群没能理解马克思本意的可怜虫。
以上这些,便是史博德脑袋中的马克思,一个“真实”的马克思,在史博德先生的理论中,我们看不到一点人类活动的踪迹,一点踪迹也没有,甚至连人的脚印都没有,私有制这棵大树自己茁壮成长最后变成了另一个物种,在这期间人类不需要插手,更不需要什么政治革命。在史博德先生的脑袋里,马克思的思想精髓就是一种神秘的关于末日审判的预言,只有读完马克思的全部手稿,才能领会先知马克思的真实想法。史博德先生绝不是公知,公知是拼命地证明马克思错了,而史博德先生则是向我们展示马克思是如此地睿智,以至于恩格斯、列宁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理解他。公知们让马克思下了地狱,而史博德先生则把马克思摆到了天国,总而言之,马克思不在人间。
但是,马克思的思想仅仅是老学究们的思维游戏吗?马克思的学说仅仅是一种类似《红楼梦》研究的课题吗?马克思难道就是一个成天嘟囔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规律必报”的先知吗?马克思主义仅仅是把社会和人抽象为某些观念和术语从而把各个阶级相互斗争的历史演绎为某些原则的打斗吗?如果马克思主义真的是这样,那么我就要说:“对不起,我不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走出书斋的、弥漫着酸腐气息的马克思主义,连一块小石头都无法搬动。”
还是让我们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吧!回到这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资本和雇佣劳动构成其两极的现实世界中来吧!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有一群酸腐的知识分子,他们最喜欢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遨游,最喜欢吃精神食粮,虽然他们饿了也要吃饭。倘若这物质食粮不合口味,他们也会不高兴,也会骂娘:“割不正不食!”但是他们吃饱了抹抹嘴,依然会嘟囔着什么“饿死事极小”“劳心者治人”的箴言,继续去构建只有他们能看懂的精神王国,然后自己给自己加一顶“哲学王”的冠冕。在现实世界中,为数最多的还是被雇佣的劳动者,他们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过活,他们为老板们创造了丰厚的财富,自己却只能拿到很小一部分,他们被房贷、车贷、子女教育费用的绳索牢牢地捆绑在工作上。雇佣劳动者被资本锁链紧紧夹住,动弹不得,“辞职去看世界”基本是虚无缥缈的“诗和远方”。一轮又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带来的只是打工仔和实习生们一大早起来去地铁沙河站排半小时队的悲惨现实?千万高楼平地起换来的只是农民工的露宿街头和平民百姓的“望楼兴叹”?经济连续增长的奇迹难道必然伴随着农村儿童的孤苦无依和“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不!除了资本主义,人类完全可以有另外一个选项,那就是彻底消灭剥削劳动者的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劳动者的根本解放。在被剥削的劳动者中间,也有一部分掌握知识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脑力、知识或特长参与社会财富的生产过程,他们所得到的工资一般也多于体力劳动者。在这些靠笔头、键盘和PPT吃饭的人中,有一批人拒绝生活在理念的世界里,他们看到了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而人是被分为不同阶级的(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老板和雇员)。他们能够看到雇佣劳动者的苦难,并且洞悉这种苦难的根源,有志于去消灭这种苦难,他们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知识分子,而是实践者。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在现实的世界中,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为谁服务的呢?是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自己去打高尔夫球的富豪们还是身体被掏空的劳动者?答案不言而喻。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为我们列举了几种反动的社会主义,而现在,我们可以指出一个新流派——“坐而论道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从来不在人迹罕至的思想国度里发明真理,而是在社会现实中总结规律。而一些研究马克思的学者们看不到“人”的存在,虽然他们也去使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套话,譬如经济基础啦、上层建筑啦、资本主义啦等等,但是当他们在谈论这些词语的时候,却忽视了社会生活中客观实在着的阶级以及阶级斗争。事实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化,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各阶级之间斗争、博弈的结果。没有劳动者的罢工和示威,便没有八小时工作制;由于工人们一盘散沙、缺乏战斗力,我们的x先生才敢大胆地放出“劳动法过度保护劳动者”的高论。历史不是自然生长的植物,历史是一盘争权夺利的棋局。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这个阶级采取了一些行动,那个阶级采取了一些反应措施,使得生产和分配关系发生了变化,从而进一步使政治和法律制度乃至整个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的变革,不论是疾风骤雨的革命还是和风细雨的改革,背后都是具体的人的活动,都是具体的阶级的活动,都反映了阶级力量的对比,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没有农民起义的教训,新王朝的统治者根本不会搞什么“轻徭薄役”和“修生养息”。当然,成日泡在书斋里的酸腐文人是看不到这些的,在他们的世界里,历史进步的发动机是企业家精神、市场和“自由契约”这些看不见摸不到的神秘力量。
史博德先生自诩阅读了无数马克思的手稿,搞出来好多玄之又玄的术语,但就是没有注意到一个简单的词:阶级。史博德先生的那套理论机器,需要一种叫做“纯粹观念”的润滑油。有了这种润滑油,史博德先生的理论机器可以批量生产各式各样的奇谈怪论:私有制可以自然而然地走向反面,政治革命实属多余等等。然而当前世界的问题怎么解决呢?“跟我去寻找真实的马克思吧!”史博德先生喊道,“只要理解马克思的真正本意,我们就可以躺着睡大觉啦,根本不需要劳动者的斗争来改造世界,私有制自然而然顺其自然就会变成另一幅模样!”还是让史博德先生自娱自乐去吧!退一万步讲,即使有一天,严谨的老学究们发现,马克思的所有手稿都是由一个神经病人代写的,这也丝毫不会动摇客观的规律和解放的真理——无论牛顿是否经历了什么“思想转变”,宏观低速领域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不管欧姆是疯子还是天才,导电体两端的电压与通过导电体的电流总是成正比;无论马克思是不是像史博德先生描述的那样精神分裂,劳动者通过斗争获得解放的前途不会改变:随着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共产主义也越来越成为大势所趋。
然而,我们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和史博德先生打口水仗。我们更要邀请大家在实际生活中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在亲身实践和吸取他人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去检验真理、修正错误、调整策略,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消灭不可持续的、掏空劳动者身体的、人吃人狗咬狗的资本主义制度。
最后提一点微小的建议,如果想要了解马克思,还是别看《财经》杂志了,不妨把阅读经典着作和参照现实、亲身实践结合起来,在流水线上当一天临时工,可以更好地理解异化和雇佣劳动的内涵。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延伸阅读:
史傅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
《财经》杂志2016年11月7日第30期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说过,“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想法,无论是对是错,其影响力均超过一般人的理解。自认能够完全不受知识影响而偏重实务之人,其实经常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位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可是,随着历史渐行渐远,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马克思的形象就像雕塑一样固定下来,令人仰望而难以接近。幸好,马克思留下来大量的手稿,可让后人深入了解一个思想家的心路历程。
“马克思手稿的流传过程非常非常复杂,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史傅德(Fred E. Schrader)先生说,“最初给了恩格斯,恩格斯交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总部,193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把它们交给了荷兰社会历史研究所。现在这些手稿已经全都电子化了,可以在英特网上找到。谁愿意研究都可以去看,只怕没人看得懂,因为马克思会几种语言,而且有很多缩写,还有他自己创造的写法,非常难以辨认。”
作为德国着名学者,史傅德是极少能辨认马克思笔迹的人,也是当今世界极少看过马克思全部手稿的学者。史傅德的毕业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马克思1850年到1860年思想转变的手稿。2002年-2012年,他作为柏林科学院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全集编委会成员,负责整理、编辑出版马克思未刊历史笔记,又有许多新的发现和心得。
在上海巨鹿路的一家咖啡馆里,史傅德先生接受本刊记者采访,详细讲述他阅读马克思手稿的认识,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马克思。
为什么1850年后马克思开始反思?
《财经》:马克思虽然在中国知名度很高,但是毕竟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人物,所以普通中国人对他个人并不了解。您在大学里上课,学生们对马克思感兴趣吗?
史傅德:我教中国学生的时候发现,他们不能接受真实的马克思。
其实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他使用的所有资料和信息都是19世纪的,但是他的思想是超前的,并不局限于要解决19世纪资本主义的那些问题。这两者是脱节的,好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和马克思不同,恩格斯是比较现实的,他要解决19世纪的社会民主党、银行国有化等问题。马克思在手稿里写道,这些行不通。马克思有大量笔记手稿,许多话题并没有和恩格斯讨论,也没有发表。通信讨论的还是两个人比较一致的观点。实际上,马克思在和恩格斯讨论当中,不断在试探到底恩格斯能接受到哪一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讨论限于政治层面,而马克思在笔记里想得更深,从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等多方面去思考。
《财经》:传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亲密无间的朋友,看来并非如此?
史傅德:他俩是特别好的朋友,但是思想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840年代他们是亲密战友,共同写了《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从手稿看,你写一段、我写一段,还互相评论。但是1850年以后明显分开了。
马克思是真正的学者,他不断在进行思想实验,也不断在试探恩格斯,看你到底能懂到什么地步,能够沟通到什么地步。可是恩格斯没有理解马克思另外的想法,所以1850年以后两人思想上已经有了分歧。但是在感情上还是一样,只是理论上求同存异。马克思自己继续思考探索。
《财经》:思想上求同存异,这种朋友很难得。
史傅德:他俩感情上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恩格斯知道马克思是个奇才,他也需要这么一个奇才。马克思也需要恩格斯,因为恩格斯是真正的行动的政治家,马克思根本不能付诸行动。另外恩格斯也确实在财力上支持他。
《财经》:您说马克思从1850年后思想发生转变,可是上世纪80年代,马克思的《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在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人们突然发现,好像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是不是马克思思想转变要更早些?
史傅德:《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实际上是马克思的阅读笔记,档案中看到的不是一本书,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它是哲学思考,讲了对人类解放,所以非常有意义。
这本书1932年第一次出版,然后大家就忘了。到了1950年代苏联解冻时期,又被重新发现,拿来反对斯大林。马克思提倡人类的解放、自由主义、个人,西方学者也拿这个来反对斯大林专政。这种观点对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也有冲击力。这本书一次次被拿出来说事,这种现象特别有意思。
在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暴力革命、无产阶级政权等主张。列宁特别欣赏这一套,列宁主义就是沿着这么一条线发展起来的。可是1850年之后,马克思进入反思。
《财经》: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会产生反思,是什么事件或者什么因素促使了他的转变?
史傅德:首先是1847-1848年和1857-1858年两次经济危机,马克思忽然认识到,这不但是经济危机,还是金融危机。金钱分两部分,10%进入个人消费领域,90%是债券、股票等资本运作。和过去危机完全不一样,这是第一次全球化的金融危机,政治革命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他意识到从此以后,经济危机不再是一个国家的事,而是全球化的。经济全球化的思想在马克思这里开始出现。
其次,法国1848年革命以后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政治经济基础是国家银行、重工业、信贷银行等。马克思原来认为,这个帝国不可能持续,早晚垮掉,由无产阶级掌权。结果与他的预料完全相反,法国社会越来越稳定。这对他的震撼非常强烈,也促使他开始反思过去的那些想法。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和蒲鲁东针锋相对的斗争。蒲鲁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兄弟,其实支持拿破仑第三。马克思要回答蒲鲁东的理论,就必须要深入思考。
“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
《财经》:从资料看,当时恩格斯坚持政治家的实践性,甚至身体力行去练骑马射击,准备打仗。
史傅德:马克思钻到他的思想实验室里,转向经济学、金融研究,研究经济危机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在此之前他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专家,真正进入研究之后,才发现和原来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
《财经》:概括地说,1850年以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什么转变?
史傅德:他越来越觉得,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是行不通的。暴力革命也只是换汤不换药,把政府换掉了,但是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可能政治革命打碎的。
《财经》: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克思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怎么看呢?
史傅德:1850年之后,马克思的思考是围绕着资本运作展开的,他从来没有给出结论。如果说有结论,就是:第一,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拿破仑第一,还有俾斯麦,在强大的市场面前都是失败者。
第二,面对金融市场,政府也是个失败者。马克思经常以嘲讽的口气在手稿里说,不论是英美还是德法,要说政治和市场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唯一的关系就是政治家被市场腐化。他非常辛辣地来嘲笑说,你政治家想要对市场做什么,只有被它腐化。并不是市场来积极腐蚀他,是政治家自己积极被腐化。
《财经》:马克思讲得特别精彩、特别重要。他有没有预见到计划经济?
史傅德:他说,理性或合理的市场解决方法,实际上是乌托邦,并不是说国家来介入就能够解决经济问题。所以,他根本不能认同后来苏联的那种所谓的计划经济。
对未来社会,马克思并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构想。他说,我们不能想象未来社会是什么样的。他强调社会自身演进,最反对国家来支配生产和分配。
《财经》:那么,马克思对私有制持什么样的态度?
史傅德:认真阅读马克思就会发现,甚至在共产党宣言里,他都承认私有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在手稿里,他特别讲私有制在18世纪对社会推动和生产力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私有制才能被全社会所接受。还有,私有制对个人的发展、对人的自由也是很重要的。他认为,哪怕你是个拿薪酬的工人,你都是个自由的人。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发展如果超越了个人消费的界限,所有制本身就不再是私有了。发展到一定程度,私有制就成为一个悖论了。
《财经》:私有财产超过了一定限度之后,就会变成社会公共财富。但是它并不是以政治的方式变成公共财富,而是自我演化的内在逻辑。是不是这个意思?
史傅德:金钱变成资本,资本进入公共领域的循环体系,私有制其实就异化了。私有财产不再私有。马克思并没有只说要消灭私有制,而是说私有制有一天会超越自己,自己否定自己。而且私有制超越到一定程度,会否定国家,而不是说通过国家干预来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社会有一种自我繁殖、自我再生产的能力。有一天社会生产将超越社会、超越所有个人的利益,超越金钱,超越资本,但必须是社会自我繁殖,政治外力不可能超越它。
“马克思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当中的作用”
《财经》:马克思在1850年代之后,参与过现实政治活动吗,参与到什么程度?
史傅德:他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起了理论引导作用,很谨慎地参与,真正参与的是恩格斯,当然他们是互相沟通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纲领是马克思起草的,但是这些纲领把他的想法简化了,二者之间有落差,也可以说是矛盾的。
《财经》:不过对于1871年发生的巴黎公社,马克思很快就写了一本书《法兰西内战》,说明他还是关心现实政治的。
史傅德:巴黎公社期间,马克思就写了《法兰西内战》,实际上是即时的反应,根本没有足够的信息,也没有经过缜密思考。巴黎公社之后,是不是无产阶级掌权了?全是猜想,没有坚实的事实基础和充分信息。
《财经》:在此之后,马克思对有些基本判断是不是有过修正或者校正?
史傅德:很难说他到底有没有反思,因为他的兴趣和注意力再一次转移到经济问题上。但是能看出来,他越来越认为政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没有什么太大作用,所以他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当中的作用。
马克思认为,国家不能占上风,不能是强者,政治也不能起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越来越反对政治控制经济,而恩格斯还是强调国有化的重要性。
《财经》: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基本原则,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公有制等等,这些东西难道不是马克思学说里面的内容吗?还是说,马克思思想里面本身也充满了巨大矛盾?
史傅德:马克思的思想其实从来不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结论。马克思的思想一直是发展的,从来没有完结。
例如,《资本论》从来没有完成定稿,第一卷有八个版本和草稿,互相矛盾。现在通行的版本是恩格斯整理定稿的。后来德国马克思全集研究小组发现,恩格斯编《资本论》第一卷把它浅化了,甚至加了很多政治内容,其中一些和马克思手稿里的内容甚至是冲突的。也不能说恩格斯是篡改了马克思的思想,权威的《资本论》版本其实是没有的,因为马克思自己留下了好几个开放性的选择。
《财经》: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史傅德:因为马克思留了几十本手稿,恩格斯又把好多不理解的搁到一边去,觉得哪个更适合自己,就选择了哪一个。
考茨基、列宁都觉得恩格斯的版本特别好,因为里面线索很清晰:先有生产,然后有交换,剩余价值,把这些都消灭以后,社会主义实现,所以他们就沿着这条线拼命往下走。但是看马克思的手稿,根本就找不着这条线索,完全是后人的主观理解。
《财经》:列宁描述的马克思主义说,资本主义的危机一次比一次大,到最后大爆炸,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马克思承认这个观点吗的?
史傅德:特别是1860年以后,马克思越来越排除了总崩溃的结论。他说,要改变一个社会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从外界用政治手段一下子来打碎它,只有在不同领域的空间里来寻找改变社会的可能性。
其结果,马克思自己排斥的观点,最后却被考茨基、列宁强化。
《财经》: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矛盾有没有提出解决方案?
史傅德:没有。在他看来,按照内在的逻辑是不可能解决的。在现行体制中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进入资本的运作,必然多少年再来一次经济危机。用实用主义的政治手段解决,他也觉得不可能。必须走出这个体系和逻辑,才能解决。但是他说,我没有想出来怎么办。
“马克思是极端的天才”
《财经》: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研究的主要是什么?
史傅德:马克思的思想研究没有主线,经济、金融只是一部分。他想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以他的手稿里头什么都有,包括电力、化学、文献学、生物学、地理,甚至他对数学也有兴趣。他有三大本历史手稿从古罗马社会一直到英国革命,他要研究政权传承的合法性和逻辑。
《财经》:通过阅读手稿,您认为马克思是个什么样的人?您对这个人是怎么评价?
史傅德:马克思的手稿是一个思想大实验室,实验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模式。
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但他研究得出来的结论符合今天社会的一些情况。如果好好读马克思的话,特别是他没发表的东西,都能看到他真的有一种预见性。例如,中央银行、信贷和政府债券的作用——这些是19世纪没有发生的,马克思的手稿里完全推断出来了,而且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
马克思是一个极端的天才,或者是一个天才式的“疯子”,毕生的精力都在寻找一种他不可能得到的结论。从天才性来说,他可以跟黑格尔相比,他在思考的层面已经触及了可能的边界。所有他之后的政治家,或者是在他的这条线上思考的人,都没有到达他的高度。
《财经》:怎么理解马克思思考的边界?
史傅德:对马克思来说有两方面,一个是他想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实际是什么样的,这是可触及的、相对物质层面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人的精神和思考的临界点在哪儿。他一直在研究人类意识的形态的演变,结果是相互矛盾的,这是他所触及的临界点。
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说,马克思都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或者其他政党宣扬的马克思。真实的马克思不是后来被描述的,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后来列宁他们塑造的那样。
《财经》:其实早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时候,很多德国年轻人阅读后,兴奋地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知道以后气愤地说,我什么都是,但我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史傅德:确实,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后来马克思本人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可惜没有人去好好研究,也没人理会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因为不想接受。
马克思主义者都说,马克思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是不可分的。但是,政治家必须是可以交流的,必须有听众,但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大部分东西里是无法交流、无法让听众马上明白。从这点上说,马克思不是一个政治家。特别是阅读他的手稿以后,我真的不能把这两者捏在一块,完全是两个形象。
《财经》:既然不是从事实践的政治家,所以马克思也不应该为后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负责?
史傅德:马克思思想在共产主义国家被接受的其实是很少的一部分,主要是国家革命、暴力革命之类,这些都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继承傅里叶、圣西门、欧文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1850年代对英国的经济状况研究以后,就像前面谈到的,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巨大改变。
马克思主义和后来发展下去的那些理论是另外一个历史。它不是马克思思想的延长线,而是衍生出相对独立的另外一条历史线索。作为思想家,马克思不能、也不应该为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负全部责任。
「赞同、支持、鼓励!」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cwzg.cn/theory/201612/328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