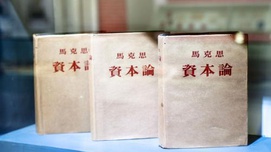社会总效率原则的意识形态及其实践后果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独家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微信公众号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一、社会总效率原则的滥用
经济学对效率的关注和强调,起源于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边沁认为,“趋乐避苦”的本能支配着人的一切行为,成为人们的目的;因此,衡量人们行为好坏的唯一标准就是功利原理: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少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而且,在边沁看来,功利原理不仅应用于私人的每项行动,而且适用于政府的每项措施,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也是实行功利的工具和手段,一项法律、制度的好坏就在于它是否能够“为最大多数人谋得最大的幸福”。正是继承了这种功利原理,波斯纳等强调,只要能使财富最大化,就是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大意义上实现了公平和正义,至于具体法律关系中当事人是否得到了公正的判决和对待则变得无关紧要了。
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几乎所有的宏观分析和政策主张都根基于社会财富最大化这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并想当然地基于成本-收益分析而主张:任何一个政策或者行为,不管让多少人受益或受害,只要其整体的成本小于其整体的收益,就具有正当性而应该被推行。例如,Layar和Glaister就写道:对经济政策进行评价“惟一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应该给成本和效用进行赋值,通过把它们相加来所决定,同时接受那些效用超过成本的项目。”[1]问题是,社会总效率原则果真促进社会正义的提升和社会福利的提高了吗?这里分别从社会总效率原则的实现方式和实践后果两方面作一剖析,首先,我们来剖析社会总效率的实践后果。
一般地,社会总效率仅仅是个总量概率,从而无法体现每个人的应得权利以及相应的利益分配,正因如此,现代经济学引入了卡尔多-希克斯补偿原则对之进行修正;但是,这种补偿原则迄今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几乎没有被主流经济学应用到实践中。正因为现代经济学并不真正实施卡尔多-希克斯补偿原则,更没有考虑现实世界中的收入分配及其其他效应;结果,简单地基于这种财富最大化的效率原则所推行的政策,往往就会给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恶果。例如,张维迎等就多次宣称,只要抓总量增加,而不必管分配,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2]但试问,在中国经济总量公认已取得跳跃式增长的今天,社会矛盾缓和了还是严重了呢?
二、萨默斯建议引起的轩然大波
我们先看一个例子,社会总效率原则在应用中所潜含的问题也就可略见一斑了。
1991年12月12日时任世界银行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的萨默斯给他的同事们发了一份备忘录,主张世界银行应该鼓励将更多的污染工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中去,并列举了三大理由。
(1)“对引起健康损害的污染的成本衡量取决于因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而失去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定量的损害健康的污染应该在成本最低的国家进行,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最低。我认为,把大量的有毒废物倾倒在收入最低的国家背后的经济逻辑是无可辩驳的,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这一事实。”
(2)“污染成本曲线可能是非线性的,因为在污染水平很低时增加污染的成本可能会非常低。我一直认为,在人口稀少的非洲国家污染的程度应该大大降低,与洛杉矶或者墨西哥城相比,非洲的空气质量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太好了。只是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实,即这么多的污染是由不可贸易物品产业(交通、发电)制造的以及固体废物的单位运输成本是这么高,阻止了能提高世界福利水平的空气污染和废弃物的贸易。与那些反对这些让欠发达国家有更多污染的提议的意见(比如说,对某些物品的天生的权利、道德因素、社会关怀以及缺乏合适的市场等)相关的问题是都可以被反过来提并或多或少地能被有效地用以反对世界银行的每一个自由化的建议。”
(3)“基于审美和健康原因,人们对于清洁环境的需求很可能具有非常高的收入弹性。如果一种诱因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会导致前列腺癌,那么在一个人们能够活到得前列腺癌的年纪的国家,人们对这一诱因的关注肯定要高于一个五岁以下幼儿死亡率为千分之二百的国家。同样的,对工业大气排放物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有碍能见度的颗粒,而这些排放物也许对人们的健康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显然,那些能引起对污染的担忧的物品的贸易是能够促进福利的。在当前的情况下,进行生产的地点很容易改变的,但对清洁空气的消费是非贸易物品。”[3]
萨默斯这封主张将污染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备忘录后来被人公开,随后引起了一场很大的风波,以致萨默斯被迫辞职。例如,巴西当时的环境部长胡赛.卢森伯格给萨默斯写了一封公开信:“你的推理在逻辑上是完美的,但根本上是疯狂的。……你的想法是那些传统的‘经济学家们’在思考我们生活的世界时所表现出的不可思议的精神错乱、简化论思维、对社会的冷漠和自大无知的具体例子。”
事实上,任何一个没有受过主流经济学影响的第三世界公民,在看见了或者听说了作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的萨默斯先生的这番言论以后,第一个反应都是愤怒,甚至会斥责萨默斯先生胡说八道,更有甚者,会有人指责这是帝国主义心态或者帝国主义言论。然而,那些受过主流经济学教育并深信主流经济学的人们却极力为之辩护,因为在他们看来,经济学研究的就是经济问题,与道德、伦理以及社会关怀等等没有关系。
问题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人的那些主张果真是价值无涉的吗?如果这样的话,为何又会招致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弱势者的反对呢?很明显,萨默斯的备忘录具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尽管有人可能会坚持“价值中立”而将之排除在经济学之外,但这个备忘录又明显与经济学有关,是基于经济学观点和理论的政策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规范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内容。
豪斯曼和麦克弗森就提出了这样八点注意:(1)萨默斯关注经济状况的评价并建议如何改善经济状况,其评价的依据是经济结果而非过程;(2)萨默斯认为存在单一的进行经济评估的体制,却并没有对这个评估体制进行具体描述和审视,而是想当然地把它视为客观的和理所当然的;(3)萨默斯使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框架来推断关于世界银行应该怎样做以及什么事实令人不快的结论;(4)萨默斯将政策和经济状况与个人福利联系起来,而没有关注对环境或本地文化的影响;(5)萨默斯主要基于经济状况而非其他方面来对个人福利进行评估;(6)在探讨福利时会主要接受了竞争市场存在时的市场衡量事物的方法;(7)萨默斯没有试图将福利的增加和减少累加起来,也没有试图对不同人的福利进行比较;(8)萨默斯主要基于经济逻辑而很少考虑“固有权利、道德因素、社会关注和缺少充分市场”等带来的反对意见。[4]
然,上述八点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已经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和文化所接受,但另一部分明显是主流经济学的独特特点,如只重视结果而忽略过程的评价标准、只关注个体福利而不关注平均福利等。正因如此,即使在西方社会,萨默斯的备忘录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豪斯曼和麦克弗森说:“萨默斯的备忘录中作为例证的经济学充满了很多具有争议性的假设。”[5]
三、社会总效率概念无视具体的利益分配
毋庸置疑,任何政策都会存在利益分配效应,从而带有价值取向。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将它所持有的价值取向视为唯一客观的和毋庸置疑的,从而就急急乎基于经济逻辑而开出政策处方,从而就造成了严重的问题。譬如,在萨默斯的备忘录中,当污染性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时,尽管对人类社会整体来说是有利的,但这并不就是对所有人都是有利的;在现实生活中的明显结果是,发达国家的人民享受了绝大部分利益,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则要完全承担这种成本。
具体说明如下:(1)现代社会还不存在一个有效进行污染买卖的市场,无法计算出污染的实际成本,如污染造成的实际伤害的信息本身就是不完全的;(2)即使欠发达国家自愿接受从发达国家转移污染而获得补偿,这种交换也并非是公平的,因为两者拥有的实际“权力”是不均等的;(3)资源交换甚至也不总是使双方都受益,因为人们的行为并非都是理性的,往往会受短期的诱惑而钟情于那些最终对他们有害的事物。也就是说,污染产业转移带来了收益分配以及效应的成本-收益之承担是不对称的,正因如此,在没有合理的利益转移机制的情况下,必然会遭到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抵制。[6]
既然如此,为什么现代主流经济学会提出如此明显不合理的主张呢?根本上,这就与它的分析思维和和相应理论有关。
第一,这与它赋予其所使用的效率概念的内涵有关。一般地,主流经济学所崇尚的社会总效率概念关注的是社会总财富的最大化,对社会总体效率的实证分析也是以大数定律为基础,从而根本无法对成本的承担和收益的具体享受进行分析,相反,还在供求均衡和财富最大化原理的支配下为那些既得利益者进行辩护。显然,这种分析充斥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几乎所有方面。例如,现代经济学在比较一个制度的优劣时往往使用交易成本这个概念,但正如格里高利.道指出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教条是,对可能采用那一种结构产生影响的只是一个治理结构的总成本,而不是这些成本在行为人中如何负担。……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效率前提的正当性可以在选择的意义上得到证明之前,我们必须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让步,那就是选择的力量不会对专断的时候集合体所感受到的成本和收益发挥作用。”[7]
第二,这也与现代经济学的抽象量化取向有关。一般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数量化倾向企图将人类所有的需求、追求乃至价值都用统一的货币来表示,从而根本没有考虑到有些价值是根本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如人类生命和健康之类就很难用金钱来衡量。桑代尔在其哈佛大学的演讲中举了一个例子,福特汽车的刹车有些问题,那么是否应该为提高安全而召回修理呢?按照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召回的成本是:每辆车11美元×12500万辆车=13700万美元;相应地,获得的收益是:180人死亡×20万美元赔偿+180人伤残×6.7万美元赔偿+2000个交通事故×700美元=4950万美元。显然,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是:福特公司不应该召回这些有缺陷的车。但是,现实情形却是:绝大多数汽车公司都会召回这些车,而且政府也要求它们召回这些车。[8]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
当然,对人类生命和健康的重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汽车召回制度也只是最近几十年才真正推广的。事实上,1971年福特为应对日本小型汽车的挑战而推出轻型廉价的平托汽车,但该汽车在发生追尾时邮箱会被车头保险杠的螺栓刺穿并起火而发生爆炸,改进的途径是在邮箱和保险杠之间加一个6.65-11美元的隔档装置。但是,福特公司在作成本-收益分析后在其臭名卓着的备忘录中宣称,赔偿受害者要比修理平托划算得多;同时,它不仅没有将追尾可能爆炸的信息告知顾客,而且也没有将是否假装隔档装置的选择权交给顾客。结果:仅1976-1977年间就发生13起追尾事故,福特公司接连被起诉损失了5000万美元的诉讼费用,远高于因不加装隔档装置而省下的2090万美元;同时,福特公司因此而在公众中形成极坏形象,这成为福特身上永远洗刷不掉的“平托门”污点。
四、结语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社会总效率原则存在明显的缺陷,基于成本-收益分析而所得出的结论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并不可行。基本理由是:(1)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都具有公共性,都会影响其他人的利益,因而任何经济政策都要考虑其利益享有和责任承担的主体,而不能忽视具体的个体来谈论抽象的整体;(2)人类社会并不是只有经济一个方面,而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综合体,因而任何政策都不能仅仅考虑经济这单一层次,而是要考虑人类社会合理而可持续的发展。事实上,即使在现代西方社会,制度设计也并非总是基于社会总效率原则,而是嵌入了对社会正义的考虑。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现代那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绝大多数公共场所都有专门为伤残人士建筑的通道、厕所等无障碍设施。为什么要盖这些设施呢?难道是基于社会总效率的考虑?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这些无障碍设施所占的空间一般要远远大于伤残人士所占的比重。正因如此,一些国人出国看到这些设施时往往会觉得很浪费。但欧美国家的人却并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基本的尊重和平等,即使伤残人士很少,他们也有与其他健康人一样方便地进出入的权利,因而社会也应该有这样的设施。显然,这里的制度原则不是效率,而是同理心,正是由于这种同理心的存在和传播,以致无障碍的观念早已根植发达国家人们的心中。
[1]Layard R. & Glaister M., 1994, Cost- Benefit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
[2]张维迎:“理性思考中国改革”,《财经界》2006年第6期。
[3]Summers L., 1992, Let them eat pollution, the Economist, 8 February, p.66.
[4]豪斯曼、麦克弗森:《经济分析、道德哲学与公共政策》,纪如曼、高红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5]豪斯曼、麦克弗森:《经济分析、道德哲学与公共政策》,纪如曼、高红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6]这里的资料和分析主要来自谢富胜,参见笔者博客:http://xueshuzhongren.blog.sohu.com/71920427.html#comment。
[7]转引自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
[8]桑代尔的演讲视频,http://www.justiceharvard.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2&Itemid=9。
【 朱富强,察网专栏学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本文节选自《效率原则是否是指导制度改革的合理原则?社会总效率和帕累托效率的实践后果解析》,《制度经济学研究》2010年第2辑。】
「赞同、支持、鼓励!」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cwzg.cn/theory/201712/400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