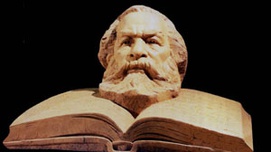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兼对当代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批判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独家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微信公众号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兼对当代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批判[①]
在当代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中,有两大理论支柱,即简单(均衡)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国内俗称“三驾马车”理论)和IS-LM理论。西方新古典综合派的宏观调控就建立在这两大理论基础之上。虽然上述理论在现实面前常常碰壁,其宏观调控政策常常顾此失彼、事与愿违(如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遭遇的滞胀,九十年代东南亚和拉美诸国遭遇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国从1996年经济“软着陆”后的“内需不足”、当前所面临的产能和货币资本过剩、房地产泡沫、人民币贬值压力以及经济结构失调,等),但仍无新的系统且科学的宏观调控理论以代替之。时代召唤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充分吸收古今中外一切科学合理的宏观调控理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是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一、对“三驾马车”理论的批判
面对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凯恩斯不像马歇尔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那样单纯地为资本主义辩护,也不像悲观的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那样对资本主义失去信心,而是试图在不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利用政府采取需求管理政策和收入再分配政策来解决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经济危机问题,即改良资本主义。这以他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为标志。他的经济增长思想或宏观需求调控思想经过希克斯、汉森、萨缪尔森等西方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的发展(尤其是与库兹涅茨发明的国民收入核算理论相结合)后,集中体现在简单(均衡)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俗称“三架马车”理论)中。[②]
在该理论中,他们将国民经济分为四个部门(消费者、企业、政府和国际部门),并假设了四个函数——均衡国民收入核算式、投资恒等于储蓄函数、消费函数和进口函数,通过联解此四个方程组(数学恒等变形),得出了如下具有代表性的简单(均衡)国民收入决定式:

其中,Y为均衡国民收入、C0为社会自主消费(即与国民收入变化无关的消费)、G为政府购买、I为社会总投资、X为社会总出口、M0为社会自主进口(即与国民收入变化无关的进口)、 ![]() 为社会边际消费倾向、
为社会边际消费倾向、 ![]() 为社会边际进口倾向。[③]
为社会边际进口倾向。[③]
在该式中,分子的前两项合在一起统称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马车”、后两项合在一起统称拉动经济增长的“出口马车”,中间I为“投资马车”;分母的倒数分别为这“三驾马车”的乘数,即C0 、G、I、X每增加一个单位,Y都将以(与乘数相同的)倍数增长;自主进口M0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这种强调政府通过促进消费、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实指货币意义上的均衡国民收入增长)的思想,又被称为凯恩斯主义。
(一)实际上是一种透支论
被西方新古典综合派阉割了凯恩斯的“消灭食利者集团”思想的凯恩斯主义,不是改变生产关系进而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方向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让在弱肉强食的市场机制作用下陷入贫困的人群增加购买力和处于弱势的产业在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上得到足够的补偿,以解决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或相对过剩)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是让这些贫困人群去借债来维持生活、让弱势产业去借债来维持再生产、让原本就已经是捉襟见肘的公共财政通过借债甚至滥发货币来促进GDP的增长。
从半个多世纪的凯恩斯主义实践的结果来看,通过“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虽然社会生产能力是提高了,但实际上是通过透支未来缓解经济危机,类似于拔苗助长、割肉补饥。大肆采用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的国家无一不是债台高筑,如美国遭遇财政悬崖、欧洲诸国遭遇主权债务危机、日本债务居高不下、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快速膨胀(包括透支执政组织的信用,货币滥发),都是很好的说明。
中国从1996年经济“软着陆”后(1995年出现了轻工产品的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或商品价值实现难题出现),为了维持经济(实为GDP[④])的持续增长,我国以“三驾马车”理论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指导,不惜大规模增发货币和大规模增加财政赤字以促进投资、人为在外汇市场上低估人民币币值和对出口加工企业实行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以促进出口、大学大规模扩招和推行按揭贷款消费等以促进消费,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地方政府、大量企业和民众都负债累累,同时,财政安全与金融安全隐患也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的不断攀升、金融杠杆过高、房地产泡沫膨胀和人民币贬值压力而累积。[⑤]透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不是什么明智之举,但西方新古典综合派却将其当作救命稻草了。
(二)脱离现实的虚构
单纯强调通过政府干预来增加社会有效需求的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在实践中事与愿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理论是虚构的:
第一,凯恩斯虽然反对他老师马歇尔的市场自动出清假设,却又用了投资恒等于储蓄这个与市场自动出清没有本质不同的均衡假设。西方新古典综合派继续了这个传统,并将过剩的存货统统定义为“非意愿投资”来实现这一假设。[⑥]这种定义,一则违背了他们所一贯推崇的经济人假设(资本家有了赚钱的机会才投资,现在居然把卖不出去的产品当作投资自己来买了!),二则是有悖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所以,这样的理论,在实践中注定是无法解决过剩问题的。

这无异于一个医生先假设病人没有病然后再给他开药方,不仅医不好“病”(经济危机)、反而导致病人“虚胖”(产能过剩、物价虚高)甚至得不治之症(个别行业如肿瘤般恶性扩张,形成泡沫经济,最终导致经济系统崩溃)。而且,就算我们认可这个“非意愿投资”概念,当实物形态财富的价值与货币形态的价值相等时,包括“意愿投资”和“非意愿投资”的投资总和,也根本不可能等于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储蓄;就算实物意义上的投资要和货币意义上的储蓄在价值上相等,也只可能是“非愿意投资”等于储蓄。总之,投资不可能等于储蓄。[⑦]详见上图1。
如上图1所示,国民收入中应该包括50亿“意愿投资”或已售出资本品。他们假定储蓄恒等于投资,即将均衡国民收入式中的储蓄通过均衡假设“乾坤大挪移”为(非意愿的)投资,但是此“投资”不包括“意愿投资”,若将该“投资”作为“意愿投资”的话,此时就又将没有全部转换为“意愿投资”的“储蓄”给漏掉了!该理论中的“投资”,其实是一个内涵不清、外延不定的让人糊涂的概念。
如果我们强制性地将价值形态上的“储蓄”用于“投资”,那么,一方面,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因为供不应求而价格飙升(此时,新增投资需求20亿,但资本品供给只有10亿。我国从2003年开始随着房地产投资的急剧扩张、铁矿石等生产资料价格的飙升,西方国家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遭遇的滞胀,都是很好的案例);另一方面,价值形态上的“储蓄”中对应的“剩余的消费品”的价值实现还是无法得到保障(虽然通过投资增加进而可能会间接地拉动一部分消费需求量的增加,但是这效果究竟如何却是缺乏可靠保障的)。
第二,该理论单纯从需求侧去考虑经济增长,忽略了现实中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所必需的技术进步、(包括人口在内的)资源约束、经济结构变化等供给侧方面的因素。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幻想。
(三)在逻辑上难以自洽
在理论推导过程中,“三驾马车”理论存在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先是用国民收入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然后用一个虚构的均衡国民收入来代替它们,结果是,现实中的经济增长问题就演变为了虚构的均衡国民收入增长问题了,市场经济中的商品价值实现难题或经济危机问题就被掩盖了。同时,将存货当作“非意愿投资”,也是新古典综合派偷换概念的杰作。
另外,西方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们先是假设国民收入分解为消费、储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之和(即所谓的国民收入核算式),然后却又将消费、政府购买和净出口等当作国民收入增长的原因,这实际上是将国民收入支出构成混淆为国民收入增长的原因了(将投资作为国民收入增长的原因,是通过假设投资恒等于储蓄来完成的)。这是利用数学等式的对称性,来掩盖经济变量之间的现实非对称性,是用数学的逻辑代替经济学的逻辑了。[⑧]
(四)本质是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
该理论不管货币意义上增加的国民收入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地改善了民众的福利,也不管净出口所得货币是否转换为实物财富以供本国居民所享用,而且还认为自主进口与(均衡)国民收入负相关,这是典型的“GDP数字崇拜”,其背后不仅隐藏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还隐藏了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
一味地通过扩大净出口来扩张GDP,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新型的殖民地主义。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推行供给外向型发展战略的、一时间曾被人鼓吹为“发展典范”“标兵”的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韩国、泰国、菲律宾以及中国台湾等,在分别遭遇金融危机而被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寡头们“剪羊毛”后,直到现在其经济社会政治仍处于动荡不安中,都是最鲜活的案例。中国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启供给外向型的发展,结果是成就了“中国人生产(赚美元外汇)-美国人消费(发美元负债)”的国际化模式。
(五)存在合成谬误
该理论还将微观主体行为(消费、投资和进口)规律当作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了,忽略了宏观和微观的分别(学界称之为合成谬误),尤其是忽略了宏观的结构性特征(如宏观消费、投资及进口与收入分配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规模及其结构等因素的关系),忽略了经济健康增长实际上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的结果(正如系统论的一个基本命题所言,“结构决定功能”)。
在该理论中,他们还无视不同产品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如房子是不能代替粮食的),将经济增长偷换成了均衡国民收入(GNP)的增长;在中国,“三驾马车”理论推崇者还无视外国在华收入与中国在外收入之差,通过GNP与GDP的“惊人”相近,进一步地将经济增长偷换成了GDP的增长(所谓“不求所有但求所存”的观点是也!)。[⑨]也正因为如此,我国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尤其是2003年以来),一方面是GDP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是“中国民众很淡定”(因为跟他们的生活改善没有多少关系[⑩])和我国经济结构的失调,以至于优化经济结构成为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之一。
二、对IS-LM理论的批判
“IS-LM”理论在本质上仍然是凯恩斯主义,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对(简单均衡)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进行阐述的主要工具”[11]。它与简单(均衡)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不同之处,似乎主要在于以下两点:一是“弥补”前者的微观基础,二是说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均衡条件下的“作用机制”(尤其是说明其有利而无害)。该理论在假定的投资函数、货币需求函数和货币供给函数(所谓的微观经济)基础上,引入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并得出由IS曲线和LM曲线组成的IS-LM模型(如下图2所示)。
该理论认为:通过综合运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就会增长、且无任何弊端和不利——先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IS→IS´),以促进均衡国民收入的增长(E1→E2),然后再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LM→LM´)将利率降下来,同时又进一步促进均衡国民收入的增长(E2→E3),详见下图2。

(一)继续了“三驾马车”理论的虚构特征
从事实来看,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通过扩张的宏观调控政策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其结果不是滞胀、就是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我国2003年以后的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累积、货币严重过剩与人民贬值压力、经济结构失调等,很大程度上都是长时期实行扩张的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政策所致。从理论上讲,它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虚构:
第一,该理论的前提——投资函数、货币需求函数、货币供给函数、以及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全是假定的。[12]而且,这些假定的前提性的函数与真实宏观经济中的投资需求和货币供求机理相差甚远。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产品市场均衡和货币市场均衡条件是纯粹的虚构。虽然,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的供求确实存在趋于均衡的内在机制,或确实存在商品供求趋于均衡的趋势,但这不代表商品的供求在事实上是均衡的。在现实经济的动态演变中,情况经常是某一历史条件需要的均衡尚未实现、而新的条件又出现了。
第二,货币的供求相等,在现实中还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究竟是有多少货币供给就有多少货币需求呢,还是有多少货币需求就有多少货币供给呢?很显然,货币的供给机制和货币的需求机制并不是统一的,市场经济中缺乏保证其相等的可靠机制存在。
当然,信仰该理论的人会辩护说,“我的积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有利而无害的结论,就是建立在‘这些’条件下的,你的现实条件不满足我的假定条件,以该结论来指导实践不理想也不能说明我的理论是错的”。这就是典型的削足适履。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原则、经济学经世济民的致用性,他们似乎也不管了。他们鼓吹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时,却从不说清楚该政策有效的前提是不符合现实的、甚至是虚构的。
(二)为了结果而不惜违背常识假设前提
为了得到均衡国民收入与利率分别成负相关和正相关的IS线和LM线,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们假设的投资函数和货币需求函数,还违背了基本的常识。
常识告诉我们,引致投资(即受到利率影响的投资)不管它多小,都不会为负值,即社会总投资不可能小于自主投资。然而,在IS-LM理论的投资函数中,无论利率多小(只要是大于零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系数或边际投资倾向也是大于零的),那么,社会投资总额都要小于自主投资(因为他们假定: ![]() ,其中,d为边际投资倾向,r为利率);否则,投资与利率之间就不是负相关了,IS曲线就不是图2所示的向右下方倾斜了。
,其中,d为边际投资倾向,r为利率);否则,投资与利率之间就不是负相关了,IS曲线就不是图2所示的向右下方倾斜了。
其货币需求函数( ![]() ,其中,k为货币的交易需求系数,h为货币的投资需求系数,r 为利率)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如果没有了如此相关性相反的两条曲线(IS和LM曲线),西方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们就无法通过什么“两条曲线的相交”来掩盖实际的市场交换机制了。这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鼓吹什么“假设无所谓对错”的工具主义方法论的内在逻辑。
,其中,k为货币的交易需求系数,h为货币的投资需求系数,r 为利率)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如果没有了如此相关性相反的两条曲线(IS和LM曲线),西方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们就无法通过什么“两条曲线的相交”来掩盖实际的市场交换机制了。这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鼓吹什么“假设无所谓对错”的工具主义方法论的内在逻辑。
(三)“专业经济学家”玩弄数学伎俩
对于“IS-LM理论”,其作者希克斯后来也是彻底否定了的:“IS曲线所表达的是流量关系,它必须涉及时期(如我们所看到的),就像我们所讨论的年度。但LM曲线所表达的是或者应该是存量关系,即平衡表的关系(像凯恩斯所正确坚持的),因此,它必须涉及时点,而不是时期。这两者怎么可能相互均衡呢?”[13]
甚至于,希克斯还对此后悔是上了凯恩斯的当:“《通论》是他向专业经济学家推销他的政策的一个途径。《通论》是精心炮制的,是按照专业经济学家的思维习惯最精心地炮制的。……它提供了这样一个模式,按照这个模式,专业经济学家能够方便地玩弄他们的惯用伎俩。他们不正是这样做了吗?通过IS-LM,我自己也掉进了这个陷阱。”[14]
总之,由于西方新古典综合派站在劳动人民立场对面、不愿意象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从生产关系去探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不敢正视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因素、对马克思主义之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视而不见,因而他们也只能通过杜撰各种内涵不清的概念、违背常识的假设、以及混乱的逻辑来获取他们想要的结论,并用这样的谬论来构建他们的“宏观经济学”,以欺骗广大劳动人民和第三世界国家。[15]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就是“皇帝的新衣”,只能依靠欺骗世人和呵斥别人不懂来维护其“正确性”了。这意味着,作为社会主义的和第三世界的中国,绝不应该套用西方新古典综合派的“宏观经济学”及其相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和政策,而应该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并构建相应的宏观调控理论、机制以实行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年的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虽然对“保GDP增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将我国经济系统陷入了一个非常严峻的境地(甚至是捉襟见肘的困境):一方面,积极的货币财政政策对拉动GDP增长的效果越来越弱,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弊端(相对过剩和相对贫困或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日益加重,同时,还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区域和城乡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乃至人口结构的失调,货币严重过剩、地方政府债务快速累积、房地产泡沫严重、资源过度耗费,严重威胁到了我国的金融安全和财政安全(当然,这些问题也不完全是因为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所致了,但是,至少可以说它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对解决这些问题苍白无力)。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理论,已是现实的需要。下文分别从理论基础、目标、体系以及政策手段四个方面来阐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
(一)理论基础
命题一:由于市场机制存在缺陷和弊端(通常称为市场失灵)[16],故需要立足于公益的(或社会主义性质的)、由执政组织来执行的宏观调控。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市场机制存在缺陷和弊端,既是宏观调控的理由,也决定了宏观调控的功用和方向——抑制市场机制的弊端、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实行社会主义。这与西方新古典综合派的宏观调控的功用和方向(保GDP增长,实质是保资本利润)不同。
命题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需要立足于中国及其劳动人民的利益立场。这既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帝国主义环视、国家主体依然存在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同时还是实现中国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的国家治理目标所决定的。这也与西方新古典综合派的宏观调控所隐含的利益立场(资产阶级乃至西方帝国主义者的立场)不同。
命题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核心,是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以引导资源和社会产品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包括人口在内的中国社会再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人本主义的要求。这与西方新古典综合派的宏观调控核心——通过透支未来的金融财政手段以期GDP的不断增长——不同。[17]
命题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主体,是包括党中央、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国有-集体经济组织在内的执政组织,它不仅要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还要行使立足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立场的国家治理的权能。这与西方新古典综合派的宏观调控主体——充当“守夜人”的政府——不同。[18]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目标
我国经济要能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已成为共识。而要转变发展方式,首先需要我们转变发展观念,而转变发展观念又需要从转变宏观调控的目标开始。
第一,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宏观调控的根本目标应该是实现共同富裕,即缩小不同家庭、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这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所有其它的宏观调控目标,都要围绕该目标而设置。自然,稳定物价水平是该目标的题中之义。因为物价水平的上涨,经常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而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正如老子所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19]马克思主义所推崇之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人所推崇之“天道”,不谋而合。
第二,经济安全应该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
宏观调控,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应紧紧围绕财政安全、金融安全、就业安全、粮食和能源等战略物资(供给)安全而展开。财政赤字在和平时期应该有个严格的限制;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有生有灭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如人体之小感冒一样),大有不必一有企业倒闭国家就要用财政资金救市。金融系统是不能允许资金大规模快进快出的(更不能允许外币形式的金融资本来冲击中国金融系统),让金融系统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位;这意味着金融系统是不能按照市场机制牟取暴利的,否则,实体经济垮在先,金融系统垮在后(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粮食作为具有公共品属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的产品,需要国家宏观上管控和保障其供给(包括数量、质量和价格三个方面)。与粮食类似的战略性物资还有能源等。
就业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根本性的宏观调控目标的基本要求,道理很简单:若大量劳动人民不能就业,单说为了安民(还不要说共同富裕了)就需要增加财政支出的负担;同时,大量的劳动人民不能就业,还是资源的浪费。也就是说,产业的发展要考虑人口规模,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不可或缺的内容。然而,将就业安全寄托在私人企业上是不靠谱的。所以,社会主义中国的就业安全,要求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必须占国家经济的主体。在当前经济形势不景气的情况下,也只有大力扩张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才能为我国就业安全提供保障。
再说,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而言,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占国家经济的主体、控制有关国计民生的要害产业,是其基本要求,也是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保障。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经济安全目标中,还应蕴含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安全的内容。这也是为了避免犯“颠覆性错误”的基本要求。
至于国际收支是平衡还是略有盈余、或是逆差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同样要服从于上述经济安全的目标、立足于国家利益和人民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随机而定。[20]财政部仅仅为了出口创汇甚或推动GDP的增长而大规模补贴出口加工企业,是不合适的。
第三,经济结构优化(或经济系统运行协调健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关键目标。
经济结构的优化,除了收入分配结构优化的内容外,还有不同产业和区域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国内国外之间的经济结构的优化。没有不同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健康,一国之经济系统是难以可持续发展的。虽然在某个特殊的历史条件或地理条件下,重点发展某个产业、重点发展某个区域的经济,是有必要的,但是不同产业之间、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存在内在的相生相克关系[21],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然而,这只有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才能解决。这与忽略了产品差异等结构性因素、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是不同的。
忽视经济结构优化、仅局限于规模总量的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犹如是只管病人体重增加、而不管病人的五脏六腑是否调和、也不管人体的各个器官和肢体是否健康的昏庸医理,如长时期片面发展工业、片面发展城镇经济、片面优先发展局部经济、片面强调GDP的增长,都是违背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目标的,更不要说放纵外资在本国的发展了。[22]这也是中央提出“经济新常态”强调调结构的用意。
在经济结构优化的宏观调控目标中,还应该考虑具体产业的产能是否过剩。并不能引起经济系统性危机的略微过剩是正常的,尤其是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生活的历史时期,基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保持一定量的剩余(实物财富储蓄),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要考虑未来的风险。也就是说,并不是一出现产能过剩而出现亏损了,就把这些所谓的“黄昏产业”给抛弃了、或让其在市场经济中自生自灭。虽然从理论上讲,经济总量是可以不断增长,但是具体到某个产业、某个产品,其产能总是要面临社会需求的限制的。中国当前遭遇的中等收入水平抑制(通常称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正是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使得诸多产业已经面临饱和所致。可当代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却用“非意愿投资”这样的神定义来逃避这一客观规律。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体系与政策手段
要实现上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目标,就需要相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及政策手段作为支撑。结合我国当代基本国情(如货币已不是金银、人口规模庞大、经济运行远比以前复杂和社会化大生产、帝国主义者虎视眈眈、经济全球化、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生活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面临中等收入水平抑制、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等),作者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体系和政策手段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金融部门、财政部门和国有-集体经济组织构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三大支柱。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绝不应该与私人企业一样仅仅以利润为导向,还应该承担公益性职能。
第二,金融部门负责货币的适量供应以稳定币值(而不是保GDP增长)。金融部门既要避免出现因为货币供给过量而带来的货币贬值,也要避免出现因为货币供给不足而带来对社会生产的抑制,即在保证币值稳定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发行货币(因为货币在社会再生产中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
就中国当前货币资本严重过剩、人民币贬值压力大的情况下,执政组织应严控商业银行货币创造(如禁止各种按揭消费贷款[23])、通过国有企业行专卖和平准之策从市场回笼货币以优化宏观资产负债表(扭转执政组织调控经济能力不足的局面)。就我国当前中美金融对决的特殊情况而言,为了避免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人民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提供足够流动性(备付),同时刺破房地产泡沫和禁止投机进而降低宏观经济的金融杠杆率、狙击热钱、增强社会对人民币的信心是必需的。
从长期来看,要消解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所致的货币严重过剩和泡沫经济带来的金融风险,唯有执政组织推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消除暴利、禁止投机、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降低经济的商品货币化程度;而不是相反——金融深化和高度的商品货币化、无条件收储外国货币;更不能在人民币国际化旗号下,推行什么人民币自由兑换和对外开放资本市场。[24]这要求我们必须首先抛弃西方新古典综合派之“三驾马车理论”以及相应的宏观调控。当我们把消费、投资和出口当作经济增长的“马车”而盲目追求GDP增长时,自然就掩盖了货币过度扩张带来的隐患和外国货币资本的帝国主义特性了,自然就要无条件地收储外国货币而不顾及货币的国家主权性了。[25]
第三,财政部门负责利用税收和补贴政策,平抑不同产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以保障包括人口在内的必要的社会再生产能够得到持续。财政补贴方向要由以前的锦上添花、保GDP增长导向,向立足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雪中送炭、保社会再生产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26]
至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乃至财政安全问题,将债务转嫁到中央财政头上以维持地方政府财政运转和剥离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做法,只是暂时的治标(当然,试图不为透支未来付出代价,那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根本的解决之道,是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系统变革我国财政体制——取消分税制,加强中央统筹力度与范围,通过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并由其利润上缴以保障国家财政有稳定充足的收入,同时节约开支(着重是遏制地方政府GDP扩张冲动、严控地方政府负债投资规模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27]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就不对私人企业征税了,只是说社会主义的国家财政不能将财政收入的保障寄托在对私人企业征税上。
只要扭转了现有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让国家财政保持盈余态势,现有的地方政府债务就不会引发财政系统性危机。
第四,国有-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仁不让地分别承担起以下四类重要职责或职能:(1)平抑物价(中国古代之平准政策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然具有合理性,任由资本追逐暴利有悖于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而且,事中调节市场交换是一个直接有效的收入分配手段、也可减小事后调节的压力);(2)保障民众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基础性产品(如粮食、食盐、水电、住房、医疗、教育、殡葬、金融、钢铁、通讯、铁道交通运输和城市公共交通等)的足够廉价供给(这些行业因其具有极大的公益性,国有-集体经济应主要体现其公共事业性质、兼顾企业属性,即对国内民众不以赚取利润为目的、采取微利运营原则);[28](3)保障有关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品(如国防工业产品等)的足够廉价供给;(4)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积极开拓盈利空间大的新兴产业、出口产业和奢侈品产业,提高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做大做强国有-集体经济。[29]
执政组织不在生产资料分配、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各个环节倾向于共同富裕进行调控,而仅仅靠财政手段在收入的再分配环节进行逆市场调节,必然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债务居高不下,就是最好的例子)。[30]这也正是“平准”之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在。
第五,对趋于饱和的有关国计民生的弱势产业[31],由国有-集体经济控制其关键的供销环节以大体上统一计划生产规模,同时限制地方政府独立投资权能,以避免地方政府和私人盲目投资和制造泡沫经济。那些认为“夕阳产业就应该放弃、其产品由其他国家来提供”、“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和南非等低收入国家转移”[32]的观点,或许对于小国而言和从跨国垄断资本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是对于有近9亿劳动人口的大中国和从实现中国可持续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的国家治理而言,却都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不能无视规模庞大的中国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和国强问题。
美国、日本、希腊等国现在所遭遇的产业空洞化问题(就业安全问题无法解决,对外依赖程度提高,并导致其国际谈判势力下降和本国经济的脆弱性加强),以及美国现在要重启工业化,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9亿劳动力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农业、纺织业等)来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以实现就业安全,并为共同富裕和资源的充分利用奠定基础。同时,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自给能力,在国际上是很难独立自主的,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这也正是“产能过剩,不能一去了之”的道理。

事实上,对趋于饱和的产业而言,在新兴产业面前自然是弱势的,除了采取国家垄断或者国家统一计划外,在弱肉强食的市场机制作用下,根本无法逃避衰退的命运。这也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科学论断所蕴含的道理。然而,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当前,大量的私人经济的存在,不少产业要重新回归国家垄断既无必要(私人经济成分的存在,毕竟可以增加市场经济的灵活性)、现实可行性也小,所以,只有由国有-集体经济控制其关键的供销环节以大体上统一计划生产规模这一条道了。这也是唐代刘宴等人在“盐铁专卖”基础上发明的“榷商”政策给我们的启发。
只有构建起如上所述(及上图3所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体系,才既可以适度发挥市场和私人经济的灵活性,又可以适度发挥中央计划和国有-集体经济的稳定性;才既可以避免市场和私人经济的盲目性造成系统性的产能过剩及其带来的经济震荡,又可以避免在新兴产业大一统的国家垄断存在的活力不足。这既符合“凡事都有两面性”、“凡事的关键在于度”的基本哲学命题,也是古今中外经济实践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四、结束语
当代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仍然是庸俗经济学家们欺骗世人玩弄数学的把戏,其“理论”的背后,蕴含的是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向第三世界国家灌输的殖民地主义意识形态。[33]
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生活或面临中等收入水平抑制的新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13亿人口规模、国际环境条件日趋恶化等基本国情下,要实现中国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需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以共同富裕、经济(乃至政治)安全和优化经济结构为目标,以金融部门、财政部门和国有-集体经济为支柱;这三大宏观调控支柱紧紧围绕这三个层次的宏观调控目标,综合运用中国古代先贤发明的“国家专卖”、“平准”、“榷商”政策和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实行过的“国家计划”政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不仅要“调”,更重要的是要(在生产规模和产品价格上的)“控”。
参考文献
[1]求是杂志社编:《求是——社论评论言论选编2015》,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年。
[2]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中央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4]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5]孙翊刚,王文素主编:《中国财政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6]刘明国:《经济长期增长研究——以谈判势力为重心的分析》,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
注释:
[①]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特色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14XKS001);贵州财经大学与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联合基金项目“基于绿色发展视角的中国农村经济模式研究”(2015swbzd17)。
[②] 但凯恩斯的消灭食利者集团的思想,却被西方新古典综合派给抛弃了。
[③] 如考虑政府部门的税收和转移支付行为,该联解方程组还可以变换为 ,其中,tr为政府转移支付(即各种财政补贴)、t为税率;此式增加的经济政策含义是,增加政府转移支付、降低税率都有助于拉动Y的增长,这实际上意味着,推动Y的增长可以减少政府收入和增加政府支出。但如此下去,赤字财政就是必然(希腊、西班牙、冰岛等国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就是最好的实例)。
[④] 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国民经济核算中,国民生产总值GNP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惊人”的相近,以至于在“三驾马车”理论中的经济增长目标GNP也就“转换”为GDP了。
[⑤] 注1:2013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高达27.56万亿元,2014年预测值是30.28万亿元,远超当年财政收入12.92万亿元和14.37万亿元(李扬,张晓晶,常欣:《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50页);注2:从1996年开始,我国的M2/GDP就超过1,并一直上升到2015年的2.06。
[⑥] 新古典综合派定义:意愿投资为在市场机制下资本家自愿进行的投资;非意愿投资为所有资本家在市场机制下不愿意的投资——存货。
[⑦] 对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这一致命假设的批判,详见王朝明,刘明国:《对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均衡假设的反思——从凯恩斯的投资恒等于储蓄说起》,《经济学家》2007年第4期,第53-58页。
[⑧] 刘明国:《对经济学数学化的反思》,《特区经济》2009年第3期,第282-284页。
[⑨] 廖子光也有类似的观点,参见[美]廖子光着,林小芳、查君红等译:《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⑩]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没有平等地分配高速增长的GDP带来的国民收入,我国基尼系数,2003年就达0.479 ,到2014年期间一直维持在0.4以上;二是,在我国从1996年后、尤其是2003年以后的GDP中,出口和固定资产占比过高,可供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消费的产品比例较低,比如,2014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就占了GDP的80.5%(而2000年时才仅占33.0%),出口占非固定资产投资GDP的18.9%(而2000年时仅占3.7%)。
[11] 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下册),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第513页。
[12] 实际上,还包括类似于“三驾马车”理论的两部门模型中的均衡国民收入函数(y=c+s)和消费函 数( ![]() )。
)。
[13] J.Hicks:Money,Interest and Wages,Collected Essays on Economic Theory,Basil Blackwell,1982,Vol.2,p.16.(转引自马工程《西方经济学》编写组:《西方经济学》(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5页)
[14] [美]希克斯:《经济学展望》,余皖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51页(转引自马工程《西方经济学》编写组:《西方经济学》(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5页)。
[15] 至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中的另一理论支柱——AD-AS理论,其荒谬性是显然的,因为他们为了对西方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所遭遇的滞胀给出一种解释,不惜抹杀宏观经济中的供给和需求的结构性差异、以杜撰出总需求(AD)和总供给(AS)概念,并以错误的IS-LM理论为基础来推导出AD和AS曲线,和继续沿用马歇尔的供求均衡假设、以虚构出总供求曲线的相交(以此来掩盖宏观经济中的种种结构性问题)。
[16] 之所以作者要用“市场机制的缺陷和弊端”来代替“市场失灵”,乃在于,(1)“市场失灵”的说法似乎认为市场机制的问题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效果不佳或者存在局限,但事实上市场机制远不仅如此,而是总是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弊端——如相对贫困、包括人口在内的相对过剩及其带来的资源浪费、弱势产业衰败和产业结构失调、经济危机乃至由此引发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等;(2)“市场”是 一个空洞的或似是而非的概念,而“市场机制”才是一个内涵清楚的概念,我们要探讨的对象是“市场机制”而不是“市场”本身。
[17] 中国1996年以来,GDP不断高速增长而民众在就业难、以高房价为代表的高物价下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甚至出现新型贫困群体的事实,也说明这样的经济增长非人本主义。
[18] 西方新古典综合派之“政府-市场”二元论,本质上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隐含了市场(实为资产阶级)为主、政府为辅(充当“守夜人”)的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抛弃这一两分法,旗帜鲜明地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组织的国家治理权能——维护公平正义、致力于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否则,将无法逃出“在经济景气时自由放任”(“市场”既然干得好,还要政府干什么呢?)、“在经济衰退时政府救市”(市场既然失效了,政府再不出来收拾烂摊子,经济就要崩溃了,那就是政府干得不好了!)的逻辑窠臼,从而使得国家治理和社会主义没有了立足之地。
[19] 参见老子:《道德经》,陕西楼观台道教协会编,内部资料。
[20] 至于如何通过汇率的变动、产业政策的调整以及对外投资等来实现对外收支的平衡,由于受篇幅的限制,另文再论。当然,中国人民银行抛弃强制性收储外汇政策,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值得肯定的。
[21] 刘明国:《中国特色最优产业结构理论》,《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48-54页。
[22] 对中国特色的最优产业结构,详见拙文《中国特色最优产业结构理论》(《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48-54页)。
[23] 对于城市住房问题,政府应该通过强化社会主义的住房政策(如大规模提供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来解决。至于我国当前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面积标准过低、完全忽视了一个正常家庭往往是三代人的人口规模的客观事实的问题,另文再论。
[24] 我们经常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也不是可以自由兑换的,比如,我们拿美元到美国去兑换人民币或黄金,美国就不会给你这个自由的。所谓的美元自由兑换,实际上仅仅是美元可以到其他国家去兑换他国货币的自由,本质是美元霸权。而现在有人鼓吹的人民币自由兑换,却是跨国垄断资本在华持有的人民币自由兑换美元。
[25] 至于如何全面破解我国当前的金融风险问题,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可见拙文《美元强势?“指数升值”注定是昙花一现》,《察网.中国》,2016年11月21日;《中国金融政策之我见——有感于人民日报<警惕金融业过度发展>》,《乌有之乡网刊》,2015年5月30日;《略论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市场完全开放》,《乌有之乡网刊》,2015年4月30日;《中国汇率政策之我见》,《乌有之乡网刊》,2015年4月13日)。
[26] 刘明国:《论“新常态”下中国财政变革的方向》,《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10期,第38-45页。
[27] 详见拙文《论“新常态”下中国财政变革的方向》(《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10期,第38-45页)。
[28]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行业就绝对不允许私人企业经营,只是私人企业被特许经营这些行业时,不能任由其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通过市场机制定价,而必须遵循“公益为主的微利原则”。这也符合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公共品,私人企业也是可以提供的。关键在于,企业运营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
[29] 刘明国:《论“新常态”下中国财政变革的方向》,《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10期,第38-45页。
[30] 刘明国,潘永波:《共同富裕视野下政府与市场的分工》,《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51-58页。
[31] 如农业、纺织等已经趋于饱和的弱势产业,现在面临过剩的钢铁、水泥、光伏等行业。
[32]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5页;《一味反对产业政策就是不负责任》,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发言,2016年9月13日,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6-09-13/zl-ifxvukhv8254883.shtml。
[33] 余斌甚至认为,“西方经济学已经丧失了(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残余的科学性,纯粹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余斌:《西方经济学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红歌会网,2016年8月15日,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6-08-14/119259.html)。
【刘明国,察网专栏学者,经济学博士、教授。本文首发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3期】
「赞同、支持、鼓励!」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cwzg.cn/theory/201803/417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