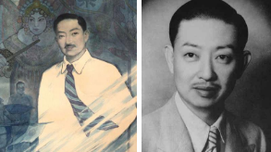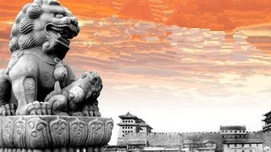“甲午”:中国、日本与“海归”

1894年9月17日,自长山串锚地出发搜索中国海军主力的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大东沟海面与北洋舰队遭遇,爆发了黄海海战。此役中方先后有14艘舰艇参战,管带(舰长)中有7人曾在英美两国留学或接受海军专业培训;而日方参战12艘舰艇的舰长中,虽然只有东乡平八郎一人是留英出身,但同样亲历此役的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大本营参谋官伊集院五郎、联合舰队参谋岛村速雄等人也拥有在英美留学或见习的经历。加上服务于双方军工、后勤乃至军事教育机关的诸多留学生,甲午战争可以说是一场“海归”之间的对决。
然而与今日国人对“海归”之学识及能力的推崇大不相同,留学生人数的多寡远未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北洋舰队的海归管带们固然不缺乏勇气或牺牲精神,但在对敌情的判断、应变能力和战术水准上并无任何高人一筹的表现。尤其是身兼主力舰管带与左右翼总兵的刘步蟾、林泰曾两人,在辅佐不通海军的提督丁汝昌做出决策时表现极为平庸,对战败的结果应付重大责任。后世史家对此往往语焉不详,他们在抽象宽泛地谈论“朝廷腐败”的同时,甚少涉及对个人履历和才能的具体评估;一方面认为“海归”云集想当然地被看作是北洋舰队富于现代化特征、中国军官个人“履历资质优秀”的表现,另一方面对如此优秀的个人协同的北洋舰队在中日海军的大较量中惨败的隐秘原因少有揭示性的探究。
直到2006年,香港岭南大学教授马幼垣在《九州学林》发表专题论文“刘步蟾和东乡平八郎”之后,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才日益暴露出来——虽然同样被称为“海归”,但北洋舰队中的留洋军官与他们的日本同行得受培训的程度大有不同,登舰实习的时长与收获也良莠不齐。然而托庇于乡谊和特殊的政治环境,这批年轻留学生归国不到十年就已升任最新型军舰的管带,且长期未再有调动,进取心、学习精神和意志力遂江河日下。反观日本,其外派学生的批次和总人数与中国几乎一致,但对“海归”始终加以反复鞭策和磨练。日本军人在结束留学生涯后,犹须自基层从头开始任职,历经多种不同类型的军舰以及岸上勤务,积累从驾驶、参谋到行政的丰富经验,方能升任指挥官之职。能力不济者在历练过程中自然遭到淘汰,所余者必是学习意识、主动性乃至精神强度都在常人之上的真正精锐。这种严格而系统的选拔和晋升制度,最终成为日本建成世界第二大海军的重要环节;而被清廷视为“奇货”的中国海归却在甲午一战而亡,留下的只有慨叹和教训。
日本:“圣将”也自磨砺出
若以开始接触蒸汽舰船、培养现代海军人才的起点论,日本比中国约早十年;1860年代后期,幕府和萨摩藩即已派员数十人赴英、荷等国学习舰船驾驶和造船技术。不过中日两国着手建立系统的海军教育制度,大致仍始于同一时期:1867年初,福建船政学堂第一期正式开班;三年后,幕末停办的海军兵学寮也在筑地恢复。1871年2月,日本第一批12名官派海军留学生启程赴英;1877年3月,中国第一批赴英海军留学生也乘“济安”轮启航,人数同样为12名。这两批“海归”后同于1878年返国,又在甲午年兵戎相见,实为惊人的巧合。
若以出国前的履历论,日本的12人年纪虽不大,但几乎都拥有在蒸汽舰船上的服役甚至实战经验,有的还是中级军官;如伊地知弘一和东乡平八郎参加过倒幕战争后期的几次海战,原田宗介是炮舰上的枪炮教官,八田裕二郎担任过海军兵学寮教官。但英国方面一来对日本的示好尚不重视,二来认为这批留学生此前并未接受完整的初级军官教育,拒绝批准其入读达特茅斯的皇家海军学院(BRNC)。这样一来,大部分留学生只能改考民间商船学校,或进入海军造船厂和军工企业充当高级学徒(当时英国仅特许少数日本贵族子弟报考正规大学)。如东乡平八郎便是在投考达特茅斯不遂的1872年,入读格林海斯的泰晤士航海训练学院;佐双佐仲、原田宗介等人则先后在朴茨茅斯、米德尔斯堡、赫尔的海军船坞和兵工厂见习,经历颇为曲折,还须忍受经费不足的窘况。

东乡平八郞
作为这批学生中最终成就最高、名声也最大的一位,“圣将”东乡平八郎的经历可谓早期日本留学生的缩影:他就读的泰晤士航海学院设在一艘1500吨的退役风帆巡航舰“沃塞斯特”号上,同班学员经常拿这个孤零零的东方人开玩笑,管他叫“强尼·中国佬”。东乡出身武士之家,赴英之前已小有战功,但为了求得一张商船学校毕业证、以争取随船远航的机会,依然从头开始经历了两年的理论学习和宿泊舰操作,至1874年方告毕业。1875年2月,东乡以实习船员的身份随三桅训练舰“汉普郡”号出海,绕行好望角和印度洋抵达澳大利亚,再经合恩角与南大西洋返回欧洲,全程超过30000英里,沿途多次遇险,还差点因维生素缺乏症而失明。对舰船驾驶这种经验学科而言,在如此漫长的航行中积累应对复杂海况的经验,感受不同的水文环境,意义极为重大。结束这次历时近一年的航行之后,东乡又转往朴茨茅斯,在英国海军历史最悠久的基地做进一步见习。1877年,日本在萨慕达兄弟船厂订购的“扶桑”号铁甲舰下水,东乡奉命前往伦敦,参与军舰的舾装监督、设备入手和接收准备工作。1878年3月,他随另一艘新完工的军舰“比睿”号归国,正式结束五年多的留英生活。
在唐德刚等通俗史家的笔下,东乡平八郎身着笔挺的白军装,在格林威治海军学院与未来的中国对手同窗求学(实则格林威治学院在东乡赴日时尚未开办),威风凛凛,哪里像真实历史那般辗转艰辛!其实首批12位日本留学生中,只有八田裕二郎在1877年蒙英国海军“开恩”,得以就读格林威治学院;余者无不如东乡一般,需要在民间海校、海军基地和工厂自行寻找学习机会,承受头脑、意志力、财力(官费发放常不及时)和健康的四重考验。有6位学生就在这样严苛的环境下无声无息地被淘汰了,1878年学成归国的仅有另外6人。
衣锦荣归远非终点,而是另一段考验的开始。东乡随“比睿”舰归国之际,不过获颁中尉军衔;在先后担任过两艘木壳炮舰的副长之后,才在1883年升任小炮艇“第二丁卯”号的舰长。1884-1890年,他先后担任过三艘炮舰的舰长,监督过一艘炮舰的舾装工作和横须贺镇守府的兵器修造,完成了一次对中国东南沿海的巡航,这才升至大佐军衔。1891年底东乡担任吴镇守府参谋长满半年后,受命接掌防护巡洋舰“浪速”号,任该舰舰长直至甲午海战爆发。换言之,学成归国足足13年后,他才获准指挥日本海军比较现代化的主力舰;而东乡正式晋阶少将,更远在对清战争胜利后的1895年,这还是考虑到他的战功。同期归国的另外5人里,除佐双佐仲后来官至造船总监(技术中将衔)、原田宗介官至造兵总监(技术少将衔)外,另两人到退休也只是大佐衔。
简言之,即使第一批“海归”在求学时的淘汰率已高达50%,日本海军也并未因物以稀为贵,就对他们的晋升予以优待。东乡虽然既具备实战经验、又有难得的环球远航历练和督造大舰的履历,但仍然要从小炮艇的副长做起,积累指挥各种中小舰艇的经验,并承担一阶段行政和参谋工作;直到军务部门确认其能力足以胜任主力舰舰长,才会放心地将最现代化的军舰交给他。至于军衔晋升,虽然要综合个人贡献和资历,但在授予将军衔时仍严格以军功为准绳,绝少通融。而求学和考核过程中的淘汰,则被视为必要的代价,并不因“人才难得”就降低标准。实际上,前几批日本海军留学生的淘汰率之高,可谓触目惊心:1871年派赴美国的4人中,仅有在华盛顿游学的坪井航三(赴美之前已经是海军主力舰“甲铁舰”的副长)日后升至将官,其余三人皆默默以终。1878年随德国军舰“维涅塔”号前往欧洲远航的第一批8名留德见习生中,只有走上层路线的山本权兵卫后来官居显赫。从1867年到1887年,日本外派的海军留学生计有留英25人、留美21人、留法6人、留德1人;在外国舰艇上短期实习的有英舰5人、美舰3人、德舰8人,绝对数量并不多。而在总数不到70人的“海归”里,甲午战前已升至舰长以上的不过坪井航三、东乡平八郎、伊地知弘一(“严岛”舰长,开战前病休)三人而已。严格的考核与晋升制度使“海归”军人在跻身领导层之后,依然必须保持不断学习的态度。如东乡平八郎在1887-1889年曾经借养病的时间,系统强化了海战法和外交法知识;日后他敢于在丰岛海面击沉“高升”轮,显然已经经过了法理考量。而东乡在自学这些法条之时,已经是大佐衔的高级军官了。
中国:“海归”在温室中腐化
当东乡平八郎前往伦敦督造“扶桑”舰之时,12名中国留学生也于1877年5月抵达英国,开始求学之旅。严格说来,他们并非晚清海军中的第一批“海归”:1872-1881年短暂的留美幼童项目中,詹天佑、吴应科等人归国后即服务于海军,甲午战争时的“济远”舰大副沈寿昌、“福龙”鱼雷艇管带蔡廷干均为留美幼童出身。但幼童在美期间所学的毕竟不是海军专业,1877年赴欧的这批学员则已经历船政学堂的近十年教育,所欲求取的也是海军驾驶、制造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进修。沈葆桢和李鸿章自1874年就开始筹划整个项目,两年后制订出30万两白银的预算,确定第一批派出30人,其中12人赴英学习驾驶,18人(含技工4人)赴法学习制造,为期三年。赴英的12人中除萨镇冰外,皆出身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一期,即中国首批按现代模式培养的海军军官。
船政第一期学员于1867年初开班,至1871年结束理论学习,转登风帆练习舰进行为期两年的远航训练(在南海和华北沿海)。1874年以后,这批毕业生已经开始在“建威”、“扬武”训练舰上担任教习。出于对他们科班履历的信任,英方不仅没有像非难日本学员一般要求中国学生从头“回炉”,还慷慨地给予了他们报考格林威治海军学院(ORNC)的机会——这所成立于1873年的新学校是皇家海军为培养高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而设,相当于海军研究生院;尽管英国在传统上更重视航海实践,但提议中国学员报考格林威治,意味着已经承认对方是合格的初级军官。然而奇怪的事就在这时发生了:船政第一期成绩最好的三位毕业生刘步蟾、林泰曾和蒋超英似乎完全意识不到机会来之不易,拒绝参加考试,申请直接上舰见习;其余9人参加了考试,有3人落榜,严宗光(严复)、方伯谦、林永升等6人则顺利入读1877年10月开学的驾驶班。由于是高级进修课程,理论学习并不繁重,1878年6月就结课毕业,随后安排登舰实习;真正在格林威治校园的时间不过8个月而已。
换言之,尽管长期以来顶着“海归”头衔,但12位中国留学生中仅有6人接受了学院深造,还是大大缩水的进修课;另外6人则不过经历了一场升级版实习而已。当然,所有12人的海上实习都是在英国海军现役舰艇上完成的,比起乘商船环球航行的东乡自是莫大的幸运,但中国学员对这种机会的重视程度依旧令人怀疑。以刘步蟾为例,1877年9月他至“米诺陶”号铁甲舰(HMS Minotaur)报到,随该舰在地中海游弋,次年12月因病登岸休养,1879年3月复登铁壳巡洋舰“罗利”号(HMS Raleigh),4个月后即启程归国。李鸿章原定用三年时间对这批学员进行特训,一年授课、两年实习,但刘步蟾满打满算也只在军舰上待了一年半而已。另一位后来成为铁甲舰管带的林泰曾则在22个月时间里连续更换了4艘实习舰,长者9个月、短者不过2个月,收获殊可担忧。至1879年底,直接登舰实习的6人与受命提前归国的严复已结束旅英之行,另外5人也在1880年5月结束舰上实习归国。随后在1882年和1886年,又先后有第二、第三批学员共23人赴英深造。

中国留学生在ORNC的成绩
刘步蟾等人在英舰实习的状况,既无报告详述、又无专业人士评估,成效殊可担忧。实际上,除去黄建勋所登的“伯勒洛丰”号(HMS Bellerophon)、林颖启等人所登的“阿金库尔”号(HMS Agincourt)曾有远航或战场警戒的经历外,地中海舰队的几艘军舰不过在寻常海况下进行巡航,锻炼效果不应被高估。而李鸿章在学员出发前即宣称“在学堂者可由师傅管教,在铁甲船者由统领官兵约束”,似乎未曾想过要有业绩评估或核准机制。后世判断这批“海归”学习成效的唯一证据,只有留学生监督李凤苞在1881年撰写的一份报告,其中将严复与从未入学校修业的刘步蟾、林泰曾和蒋超英列为甲等,萨镇冰等4人列为乙等,林永升等4人列为丙等,但不曾提供任何事理或证据支持。联想到日后李凤苞曾为北洋海军挑选式百龄(M. Siebelin)那样的江湖骗子为总教习,则他对海军显然不精通;而由这位不通军务的官僚对海军人员才能做出的评定,可靠性当然值得怀疑。实际上,曾任“无敌”号(HMS Invincible)铁甲舰舰长、后出任中国分舰队司令的弗里曼特尔上将(Edmund Fremantle)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到过他当年的实习生叶祖珪,表示中国学生在舰上并无操作技术设备的自由。由此看来,叶祖珪们虽然比东乡享受到了远为优厚的待遇,但在军舰上却只是一名看客,走马观花而已。
但李鸿章显然对李凤苞那份可靠性堪忧的报告深信不疑,12名“海归”回国后,立即以火箭般的速度得到晋升。刘步蟾甫一归国,就被任命为“镇北”舰管带;该舰虽然只是一艘守卫海口用的伦道尔式炮艇(Rendel gunboat),但已是中国最新的外购军舰。1882年,李鸿章命他前往德国督造新订购的“定远”铁甲舰,学习驾驶、指挥大舰的技术;1885年刘步蟾随“定远”归国后,立即被任命为这艘“远东第一舰”的管带,当时他不过33岁,仅有的指挥经验就是在“镇北”舰。林泰曾的晋升速度虽然略逊,经历了“镇西”号炮舰和“超勇”号巡洋舰的历练,但到1886年也升至“镇远”铁甲舰管带。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之际,9艘铁甲舰和巡洋舰里有7艘由“海归”舰长指挥,而其中海上经验最丰富的第一期留英学生,归国也不过将将9年而已。

镇远号战列舰,当时有东洋第一坚舰之称,甲午战争期间被日本海军虏获,战后以战列舰的身份编入日本海军
李鸿章视北洋海军为私器,以淮军出身的丁汝昌为提督;但他毕竟需要真正通晓驾驶技术的人员来指挥军舰,因此不得不倚重船政学堂出身的闽籍学员。当时的洋务大员曾纪泽、黎兆棠等对这批学员的人品操守多有怀疑,但李鸿章为笼络其人,依然早早赋予其管带大舰的职位,并擢升其为总兵、副将等高衔。如此一来,封官晋爵与个人能力的提升完全脱钩——实际上,北洋海军从未真正实行过以驾驶技术和指挥能力为准绳的考核办法,例行训练的成效也值得怀疑——高级将领便再无学习的动力。而从1888年舰队成军到1894年中日开战,北洋海军主力舰只的管带竟从未轮换或更替,几成世界海军史上的奇观,舰队遂日益为暮气所笼罩。
更令人扼腕的是,“海归”舰长们非但没有将英国海军的传统与榜样带回到中国,反而因为早早身居高位,形成一个利益圈子。1888年以后,闽籍“海归”管带的自甘堕落和地域主义已经发展到惊人的程度,不仅排斥邓世昌这样的非闽籍、非留英系军官(哪怕邓氏也是船政后学堂出身),甚至阴以刘步蟾为首,对抗要求整肃军纪的英籍总督查琅威理上校(William Metcalfe Lang)。1890年,琅威理与刘步蟾发生冲突后离舰,英国海军大感不满,宣布暂停接收中国海军留学生。到这时为止,已有35名中国军人自英国学成归来,另有34人曾在法国留学,与日本留洋海军人员总数完全一致。而这些中国“海归”唯一值得夸耀的经历,或许是他们晋升到将军级的比例远较日本为高——即使是何心川这样被张之洞公开上奏呵斥、称为“旷废岁月,耽误水师人才”的庸人(何氏还是第一批留学格林威治的6人之一),也能从晚清一直服役到民国,晋阶海军少将,病死在任内。李鸿章的温室政策,对海军这一兵种未曾起到任何正面作用,所肥的不过是军人个人而已。
原文载《时代周报》2014年11月25日生活版,
「赞同、支持、鼓励!」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