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拼坦克--五十军抗美援朝纪实3
【察网编者按:《三八线》热播之际,抗美援朝的话题再度成为网民关注的焦点。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的前身,是1948年10月在长春起义的原国民党第六十军。就是这支起义部队,在朝鲜战场上,特别是第四次战役期间在“三八线”以南的汉江南北两岸,于“联合国军”主要进攻方向上,以极为劣势的武器装备顽强坚守五十昼夜,打出了令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吃惊的骄人战绩。高戈里先生对此有深入研究。高戈里,着名党史专家,察网专栏作者。为抢救史料,截止2013年底,他已经采访230人。今天,高戈里先生将其研究成果独家授权察网连载发布。这篇成果,是高戈里先生在其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再版增加20万字)第九章基础上扩写而来。】
第二章:血肉之躯拼坦克
1950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美国人一手操纵的“联合国军”经志愿军第一、二次战役沉重打击,被迫撤至“三八线”及其以南地区,建立从临津江到洛东江六道大纵深防线,企图争取时间,重整旗鼓,继续北犯。
在出现“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后,1950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发表对中朝方面使用原子弹的恐吓讲话。
出于政治斗争需要,12月15日,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刚成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决定改变原休整过冬计划,提前发起第三次战役,进至“三八线”和“三七线”之间寻歼敌主力,为彻底解决朝鲜问题奠定基础。
1.向高阳攻击前进
1950年12月28日,志愿军第五十军奉命秘密前出至开城以东地域,进行战役准备。
部队战前动员口号:“敢与敌人见面就是胜利!”
12月31日战役开始,第五十军自茅石洞至高浪浦里地段强渡临津江,战至1951年1月2日,“联合国军”一线阵地被全面突破,开始总退却。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转入战役追击。
1951年1月2日晚,第一四九师奉命向高阳攻击前进。攻击高阳,既可断西北方向议政府英军之退路,又能向南直插汉城。
1月3日2时,第一四九师前卫四四六团一营配属师侦察连,在高阳以北的碧蹄里,将执行掩护任务的美二十五师第三十五团一个营击溃;随后,该营向仙游里搜索前进,并于5时攻占英二十九旅来复枪第五十七团掩护分队据守的195.3高地,俘敌37人。
英二十九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名将蒙哥马利的队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装备有最先进的“百人队长”式坦克,很有名气。拂晓后,英军以16架飞机、7辆坦克、12门火炮为掩护,发起了7次反扑,该营在付出重大伤亡代价情况下,死死扼住了逃敌咽喉,为主力抓住战机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晚,担任战役掩护任务的英二十九旅从议政府向汉城撤退。
19时,第一四九师首长急令第四四六团二营和第四四五团一营分别插入仙游里至梧琴里以西谷地截击敌人。
这场战斗,1951年2月26日的《人民日报》曾以三分之一版面予以过精彩报道。四五十年后,当年第四四五团一营教导员林家保和第四四六团二营营长杨树云讲述了这其中从未报道过,却又是最为惨烈的一幕。
那天晚上,林家保营以急行军速度刚刚插到仙游里以南的佛弥地附近,便听到了轰轰隆隆的马达声,爬上127高地一看,好家伙,山下一大串车灯像一条长蛇顺着蜿蜒曲折的公路往南移动,一支机械化部队正在撤退。
在林家保营加强指挥的团参谋长林长修当机立断,命令第一连在佛弥地以北公路东侧迅速展开,第二连立即穿过公路占领127高地对面的无名高地,从两翼夹击逃敌,迫击炮分队和重机枪分队在127高地两侧占领阵地,第三连为预备队。
命令下达后,林家保喊了一声:“二连跟我来!”带着部队趁夜暗跑步从敌行军纵队的间隙横穿过去,直扑对面无名高地。
英国人打仗真怪,知道中国军队擅长夜战,喜欢穿插迂回出奇制胜,撤退的时候,汽车一路开着大灯不说,天上还打着照明弹,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从哪逃出来,又逃往哪去似的。
第二连正好借光。照明弹亮的时候,全部卧倒,就地隐蔽,观察前进路线。照明弹一灭,一跃而起,急速向前奔跑。敌人机枪打过来的都是曳光弹,呈抛物线,看得见他往哪打,好躲。不到三分钟,百十号人一个不少,全部从敌人鼻子底下横穿了过去。
2.“揭盖盖”的喊声响彻谷地夜空
19时30分,围歼逃敌战斗打响。
第二连正准备依托无名高地附近有利地形,回头卷击敌人,忽然发现无名高地有敌掩护分队,索性一鼓作气攻了上去,边冲边喊着半生不熟的英语喊话:“哈罗,董替安克特(喂,不要动)!”
立足未稳的一个排英国兵被从天而降的志愿军吓呆了,除少数人逃走外,大部分乖乖地当了俘虏。第二连官兵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俘虏赶到一堆,还得抽出十几个人去押送他们。等他们回过头来,仅两平方公里谷地内打坦克的战斗已经白热化。

周竹贤素描:与敌坦克搏斗的英雄们
担任“拦头”任务的是第四四六团二营。那天晚上刚开战,营长杨树云和教导员高振聪就宣布:“打掉一辆坦克立小功,打掉两辆坦克立大功,打掉三辆坦克当英雄!”
口号一提出,士气大振。第五连连长阎世宝、指导员赵谦带领全连冲上公路。这个喊:“大功来啦!”那个吼:“这个大功我包了!”担任掩护任务的第四连在高地上也呆不住了,纷纷冲了下来。第四连爆破手顾洪臣,首先将先头两辆坦克炸毁在佛弥地公路转弯处的垭口。英军的机械化行军纵队随即大乱,汽车全部停在公路上,坦克、装甲车跃下公路,在稻田地里乱窜。
两个营的官兵,相当一部分人第一次见到坦克,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打坦克。部队的装备真差,不但没有反坦克火炮,就连火箭筒也没有,每个班只有一根爆破筒和一个炸药包,再就是每人背着的四枚手榴弹。手榴弹是对付步兵的。
杨树云说:坦克刚开过来的时候,每辆上面都坐着几个英国兵,天黑,我们没注意到,爆破组一上去,就被坦克上的步兵打掉了。吸取教训后,我们先组织机枪、冲锋枪、步枪的火力,把坦克上的步兵赶下来,然后,再把爆破组派上去炸坦克。
开始用爆破筒或炸药包,往坦克履带里塞。别处不行,不是弹回来,就是滚下去,搞不好,还要把自己人炸着。往履带里塞也不容易,运动着的坦克颠簸大,又是黑天,看不准位置,掉下来的时候多,爆破成功的少。没多久,爆破筒和炸药包就用光了。这时,再把四五枚手榴弹捆在一起作为“集束手榴弹”用。
林家保营第三连九班班长王长贵是长春起义的云南籍老兵,解放前,一家人尽受地主打骂,父亲的腿都叫地主打折了。部队起义后在九台政治整训期间,共产党干部组织起义官兵开展了控诉运动,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王长贵曾哭得两天没吃饭。觉悟了的王长贵在南下解放大西南歼灭蒋介石国防部警卫团的战斗中,曾带领一个班连缴两挺重机枪,遂以鄂川战役战斗英雄身份,于1950年进京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见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激动得热泪横流。
战斗中,王长贵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他爬上坦克,揭开炮塔上的盖子,刚要把手榴弹塞进去,坦克车内的轻武器响了。王长贵身中三弹,掉下车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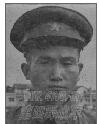
王长贵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时留影
王长贵牺牲后,反坦克手们继续爬坦克。有的被敌人发现,炮塔一转,甩了下来,坦克再急转掉头,用履带把甩下来的战士碾死。即便如此,爬坦克的人还是接连不断,“揭盖盖”的喊声依然在谷地夜空回荡着。到最后,所有的坦克都不敢打开顶盖了。
3.最难打的是“喷火坦克”
夜间伏击战,通常派上一个爆破组,最多两三个爆破组,就能收拾一辆坦克,不算太难。因为战士们拼得太顽强了。难打的是一辆“喷火坦克”。那天晚上,部队对付那个家伙,吃了大亏。
打坦克的战场是一道谷地。从议政府到汉城30余公里的乡村公路,沿谷地蜿蜒南下。公路紧挨着一条小河,两个营的反坦克手多数都隐蔽在小河沟附近的土坎下。
从议政府沿着乡村公路撤下来的英军坦克,过来一辆,河沟里跃出一个爆破组炸他一辆。连炸几辆后,敌人发现了反坦克手埋伏地点,调上来一辆“喷火坦克”开路,沿着河道“唿——唿——”地喷起火来。那是一条几十米长的火带,只要在它的射界内,躲都没法躲。喷一次火,少则烧个把人,多则能烧好几个人。
被它烧着的时候,如果能引爆身边的爆破器材,死得能痛快些。若一下死不了,呈现你面前的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火人,先在火海里又跑又跳,跌倒后,满地打滚,滚过来滚过去,越滚速度越慢,滚到滚不动了,就开始抽搐、痉挛,直到咽气,火还在燃。
眼睁睁地看着生龙活虎的战友被熊熊烈焰一口口吞噬,苦苦挣扎,在剧烈的痉挛、疼痛中惨死,在场的人又束手无策,心里的滋味真不好受!
被烧死的指战员遗体,要等“喷火坦克”开走了才敢去拖。拖下来一看,真可怜!头、肚子、腿上的肉都烧没了,焦黑焦黑的,呲着牙,胳膊、腿、身子蜷缩一团。最要命的,是这些焦黑焦黑的尸体上都呈现一种蜂窝状。开始,谁都解释不了。打完仗才发现,原来是“喷火坦克”喷火时,喷出来的铁砂打的。难怪喷火坦克每次喷火时,总是伴随着“叮叮当当”的怪动静,原来是铁砂打在石头和武器上的声音。
老人咬着牙骂:“真他妈的歹毒!”
老人咬着牙继续骂:“他们仗着科学技术发达,总是把最歹毒的武器最先用于战场,等到别人刚刚研制同类武器时,他们又打出人道主义的旗号,去制止别人。真他妈的虚伪!”
帝国主义虚伪的地方多了!他们的飞机侵入我国领空,轰炸我边境城市,却诬蔑我们侵略;他们拿原子弹恐吓我们,却咒骂我们野蛮;他们摧毁一座座城市,杀死无数平民百姓,残害战俘,却时时处处以人权卫士自居。
抗美援朝,面对如此恶敌,志愿军指战员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以命相拼,血沃大地!
自盘古开天辟地,中华儿女代代相承的遗传基因,历来不缺刑天断首、共工触山的冲天豪气,不缺神农尝草、精卫填海的献身精神,不缺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的拼搏气概,不缺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的成城众志!
敌“喷火坦克”在前面喷火,爆破手就从后面上;它在后面喷火,爆破手就从侧面上。一个爆破组通常有五人,两名冲锋枪手负责掩护,切断敌步兵和坦克的联系,其余人员分第一爆破手、第二爆破手、第三爆破手,前仆后继!
惨啊!林家保营的三连,整整一个第三排,死的死,伤的伤,基本打光。被活活烧死的,仅四四五团第一营就有15人,机枪打死的和受伤的还不算。
4.反坦克英雄李光禄
“喷火坦克”后来被第四四六团二营五连副班长,四川三台籍的李光禄炸毁了。李光禄是鄂川战役补入部队的原国民党士兵,苦大仇深,他一共炸毁3辆坦克。

特等功臣李光禄
炸头一辆坦克的时候,李光禄爆破组的第一爆破手杨厚昭先上,他从沟渠里跳出来,把爆破筒往坦克履带里一插,没插稳,爆破筒在履带里“咯咯嘎嘎”地响了几声,被甩下公路爆炸了。第二爆破手刘凤岐抱起炸药包再上。由于10公分的导火索太长,放在公路上的炸药包在坦克隆隆驶过后才爆炸,白白腾起一根令爆破手们捶胸顿足的烟柱。
李光禄没时间思索了,他果断地将导火索截成3公分长。3公分导火索,意味着李光禄必须在3秒内完成炸药包的点火、投送等动作,并迅速转身、撤离、隐蔽。前面是敌人的火力网,后面是坎坷不平的稻田地。更为困难的是,点火没有拉火管,火柴又在行军中被汗水打湿了,李光禄和刘凤岐是将棉大衣上的棉絮扯下来,到公路边被燃烧弹打燃的草地上点着,捂回隐蔽爆破手们的沟渠里,再把火种藏在棉大衣下。不但麻烦,还相当危险。
李光禄什么都不顾了,只想打坦克。
当一道眩目的闪光和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把坦克车内四名乘员送上西天的时候,李光禄也被一股热浪狠狠地推倒在稻田地里,随后,就是一块不小的冻土重重地砸在后背上。
李光禄醒来的时候,谷地四野弥漫着浓烈的硝烟,火,已经映红了半边天。他吐了两口黏糊糊的浓血,费了好大的劲才撑起右肘,侧过身子,把冻土块从后背掀了下去。
不久,李光禄又在营长杨树云的指挥下,炸毁了第二辆坦克。这一次,炸药包是用绑在上面的两枚手榴弹引爆的,时间更短,引爆时间只有不到两秒钟。他又一次被震晕在坦克车旁。
熊熊燃烧着的坦克将附近的冰烤化了,冰水浸到了李光禄的后脑勺,他昏昏沉沉地感觉到头有些冷,想找帽子戴,可是,浑身软绵绵的,一点力气都没有,骨头仿佛散了架,每个关节都像楔进了无数颗小钉,眼皮像被胶粘住了一样,怎么也睁不开。他感到口渴,顺手摸了一块碎冰,塞进嘴里,一股清凉的冰水顺着喉咙咽下肚,昏昏沉沉的脑子才渐渐清醒了。
醒了的李光禄又听到了战场的枪声炮响,以及那些听得懂和听不懂的叫喊声。“坦克还没打完呢,我不能在这躺着。”李光禄强忍难捱的疼痛,硬撑起身子,踉踉跄跄地去取炸药包。
这时,一位战友告诉他,没有炸药包了,大家正在全力对付“喷火坦克”,已经搭进去好几个爆破组了。
李光禄一听,全身热血“轰”地一下涌上脑门:“老子就不信打不掉它!”也不知道哪来的劲,瞬间又恢复了往时的矫健,提着手榴弹重新跃入谷地。
回到谷地沟渠的李光禄,手中只有两枚手榴弹,要打坦克只有爬上坦克车了。他先匍匐前进到“喷火坦克”必经之路附近的一道土坎旁隐蔽下来,待它开过来时,突然跃起,从侧后猛追上去,左手抓住车上的铁环,右手握着手榴弹并同时扶住履带上的叶子板,纵身一跳,登了上去。李光禄还没站稳,突然,“哒哒哒……”一梭子子弹从他腋下穿了过去。
“不好,让狗日的发现了!”说时迟,那时快,李光禄索性扑上车顶,一只手掀开上面的盖子,另一只手把手榴弹塞进了“呜哩哇啦”直叫唤的车内,然后,翻身跳下。
“轰!”一根粗大的火柱从“喷火坦克”内腾空而起,接着,一团一团或大或小的火球从天而降,散落四周。
“轰!”一根火柱从“喷火坦克”内腾空而起,接着,一团一团火球从天而降,散落四周。如坠火海的李光禄冲出危险地带,往雪地上一扑,就势猛滚,才把身上的火滚灭。
打扫战场时,营长杨树云看到,脸部被烧伤的李光禄正背着腿部负伤的战友刘振富撤离战场。
李光禄炸毁“喷火坦克”为步兵第一四九师高阳追击战画上了一个血红的句号。

被炸毁的英军坦克——胡宝玉摄

被炸毁的敌坦克及敌军尸体

被炸毁的敌牵引车

被炸毁的敌105榴弹炮
从此,英军战史将葬送“日不落帝国”“皇家”铁骑的这道谷地,称之为“死谷”。
5.奉命打扫战场
战斗结束后,上级命令第四四五团一营负责打扫战场。
时任该营教导员的林家保说:那是咱们这帮土包子又开眼界又得意,又出洋相又抓瞎的差事。
英军的坦克、装甲车和汽车全被我们堵在了谷地里。下了公路的坦克、装甲车多数都被炸毁了,东倒西歪横七竖八地躺在沟里、稻田地上。公路上的坦克、装甲车和汽车有相当一部分是好的,车灯开着通亮,马达还在“轰轰隆隆”地叫唤。
英国兵呢?有的被打死了,伏在方向盘上,或倒在车内;有的鸟散了!
英国兵打仗的时候挺凶,打不赢了,当俘虏却很坦然,很痛快,也蛮有大英帝国的绅士风度。
多数俘虏是喊话喊出来的。本来战斗意志就差,打了一夜,叫志愿军的“拼命三郎”们打怕了。有两个英国俘虏,从坦克里一爬出来,就用生硬的中国话一个劲地说:“艾德礼(英国首相)坏,跟杜鲁门(美国总统)跑!艾德礼坏,跟杜鲁门跑!”
有几个俘虏,是战士爬上坦克炮塔,一边用手榴弹敲炮塔盖子一边喊话给弄出来的。里面的英国大兵挺听话,一喊,就把炮塔的盖子打开了,先慢慢举出两只手,再缓缓伸出一个脑袋,一个个磨磨蹭蹭爬出来后,双手举得高高的,你不让他放下来他绝对不放下来,非常正规。
有一辆坦克,里面最后爬出来的是个什么东西?一条拖着尾巴“汪汪”直叫的洋狗!蛮有英国绅士的闲情逸致,真不知是来打仗还是旅游?
还有从树丛里抓出来的。
英军俘虏比国民党军俘虏要文明多了,有些事情配合还蛮好。

被俘英军一部
部队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基本完好的坦克、装甲车、汽车、榴弹炮还不少,停在公路上一串,马达还在轰响,车灯还在亮着。
这么好的家伙不能丢下来不管,天一亮,美国飞机就要来轰炸,炸坏了多可惜。
可是,全营官兵无一人会开,咋办?到俘虏堆去找找试试吧。
这时,上级派来的翻译还没到,对抗虽然停止了,“对话”还不能进行,只好用手比划:指指坦克、汽车,再用两手做出掌方向盘、握操纵杆的样子。
一些俘虏还挺帮忙,指了指他们中间的几个:“呶,呶。”
就这样,尚未损坏的坦克、装甲车、卡车、吉普车和榴弹炮,由志愿军战士押着英军驾驶员俘虏,开到战场附近的另一处谷地,然后,砍来松枝盖上,加以伪装。
果不其然,早晨8点来钟,美军飞机来了。
先是侦察机在头上转悠。
转悠够了的侦察机走了,直升飞机又临空了。
美国空军驾驶员真欺负人,知道志愿军没有防空火器,几乎是贴着地皮飞。林家保后来回忆说:“扔个土坷拉都能打到那家伙。”
白天是美军飞机的天下。我志愿军部队都分散隐藏在附近山上的树林里或草丛中,沟沟坎坎也都藏着人,不敢开枪,怕暴露目标,遭敌火力毁灭性的报复。
尤其是那个直升飞机,谁都没见过,让志愿军土包子们全看傻眼了:这叫什么飞机,怎么没翅膀呢?怎么能停在半空不动呢?这家伙是来干啥的?
于是,一个最大限度发挥想象力的命令传达了下去:注意这个飞机,是下来抢俘虏的,它不下来,不准开枪!
直升飞机始终没落地。
到底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王牌驾驶员,不光有胆量,经验也异常丰富。只见美军直升飞机顺着谷地的机耕路低空飞行,让螺旋桨搅起的巨大气流,将覆盖在坦克、装甲车和汽车上的伪装全部掀掉,使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随后,一批次接一批次的战斗轰炸机临空,由直升飞机校正弹着点,投掷航弹,一辆坦克丢一枚,一辆汽车丢一枚,一辆不少地炸了个稀烂。
林家保他们睁着个大眼睛,看得目瞪口呆!
回过神来后,一个个跺脚直惋惜:唉!好不容易缴获点好装备,全完了!
叹完气,再幻想后悔药:要是我们自己有驾驶员,把坦克、装甲车和汽车开远一点,就不会吃这么大的亏了嘛!
6.英军俘虏炒“硫磺”
美军飞机逞完威风飞走后,林家保组织人员继续收集战利品。
最使干部战士感兴趣的,是英国军队每个营都配有给养车,上面有不少好吃的东西,面包、压缩饼干、牛肉、罐头、香烟等等,让大家美美地解了解馋。
打扫战场的时候,正好一支朝鲜人民军路过,林家保就让战士们把一部分骆驼牌香烟和食品分给了他们。
嘿!人家那个高兴啊,一个劲儿地伸出大拇指“东木,东木”(同志的意思)叫个没完。
当然,更让人民军战友高兴并钦佩的是,路边一辆接一辆残破的英军坦克、装甲车和汽车所昭示的志愿军辉煌的战绩。
不过,战绩归战绩,洋相还没出完。
清理给养车的时候,林家保特别吩咐要多收集罐头,那东西,又好吃,又便于存放、携带。结果,发现了一种20斤装的大罐头,上面虽有英文说明,但不认得。只好用十字镐刨开,一看,里面都是黄色粉末状的东西,无一人识货。
咋办?
猜!
“是涂料。”
马上招来反驳:“胡扯!打仗带那么多的涂料干啥?”
“是硫磺吧?”
这回反驳的少了,“哦,是有点像。”
“打仗带这么多的硫磺干什么?”
“人家讲卫生,八成是用来消毒的。”
“不要!不干不净,从不生病。”一脚踢到车外雪地上。
用十字镐再刨开一筒,“他奶奶的,还是硫磺!”
又是一脚,也踢到了雪地上。
“把这堆大罐头都刨开看看,别把真罐头扔了。”林家保吩咐。
就这样,十字镐刨开一筒,踢上去一脚。一边踢一边骂:“这帮狗日的,带啥不好,净带些没名堂的东西,让我们白费力气!”
不一会,车外一地“硫磺”。
车上的战士正在对“硫磺”发气,押往后方的俘虏队伍走过来了。走到“硫磺”跟前,一个个都停了下来,“叽哩呱啦”地不知说了些啥。
把林家保他们都看愣了:难道“硫磺”里有名堂?
这时,队伍里走过来个英军俘虏,指了指地上的“硫磺”,然后,一手做端碗的手势,另一只手,做从“碗”里往嘴里扒饭的动作。
林家保他们面面相觑,“是吃的东西?”
一位战士刚要去尝尝,被林家保拉住了,“慢点,要是有毒药怎么办?你没见过美国鬼子往老百姓的村子里丢炸弹?心眼儿比国民党还毒!”
英军俘虏看明白了,走近用手指头抠了一坨“硫磺”放到嘴里,又伸出舌头在嘴边舔了一圈,然后,站起来,两手一摊,“叽哩呱啦”地又不知道说了些啥。
一位胆大的战士也上前尝了尝,对投向自己众多的目光摇了摇头,说:“甜稀甜稀的,尝不出来是啥东西,反正不是‘硫磺’。”
英军俘虏干脆在地上摆三块石头,找来一顶钢盔放上去,再找来点破布条,打开汽车的油箱盖,蘸满汽油,塞到钢盔下面,点着,然后,抓一把雪放进钢盔里,等雪化了,再抓一把“硫磺”丢进去,找一根树枝在钢盔里一搅,黄澄澄稀溜溜的“硫磺”凝固了,钢盔里飘出了一股香喷喷的鸡蛋味道。
俘虏端开钢盔,用树枝挑着鸡蛋自己吃了起来。
胆大的战士不等人家请,主动凑了上去,尝了一口,还没等鸡蛋咽下肚,就高兴地叫了起来:“妈妈的,是鸡蛋!”
林家保乐了,“快,赶快把‘硫磺’,不,把鸡蛋罐头都捡回来,给各连分下去,要快!”
其实,那不是鸡蛋,是鸡蛋粉。
洋相归洋相,林家保他们还是挺自豪:我们这群土包子,凭着落后的武器装备能打这么大的胜仗,本身就是奇迹。以后,看谁还敢小瞧咱们中国军人!
7.辉煌战绩,让统帅吃惊
1月3日晚经过三小时激战,我军歼灭英军第二十九旅皇家来复枪第五十七团一部和英军第八骑兵(坦克)团直属中队(即1951年2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的“皇家重坦克营”)全部,炸毁敌坦克和装甲车27辆、汽车3辆,缴获坦克4辆、装甲车3辆、汽车18辆、榴弹炮2门,毙、伤敌200余人,俘敌少校营长柯尼斯以下官兵227人。
这一仗下来,曾泽生相当得意:“我早就说过,我的部队还是能打的!”
8天后,彭德怀、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联名致电各军并上报中央军委,通报表彰了第四四六团。
表彰通报之所以在8天时候才下发,是因为第五十军将一四九师打坦克战斗的战绩上报之初,志司首长硬是不相信,甚至“惹”得“彭总发火了”。
47年后,解放军画报社离休干部胡宝玉讲述了他经历的一件已经被人们淡忘了的往事。
这场战斗结束的第二天,在军部担任摄影记者的胡宝玉被军政委徐文烈喊去:“一四九师歼灭英军皇家重坦克营的战果,我们向‘志司’报告了两次,他们还要我们‘再核实一下’。你马上去战场实地拍一些照片回来。由四四六团二营派李光禄所在排协助你行动。”
在第四四六团二营五连李光禄所在排的协助下,胡宝玉拍摄了一组传世的经典照片,包括李光禄排和朝鲜人民军在汉城“国会议事堂”前跳舞联欢的那张。
与胡宝玉同时赴战地核实战果的原志愿军第五十军司令部作战参谋郑竹书,讲述了他亲眼所见另一幕战场往事。
在一辆被炸毁的英军坦克上,趴着一位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的志愿军战士,烈士伸进敌坦克窗口的一只手已经被炸断,坦克内,4名坦克兵尸体东倒西歪。
由于要防敌空袭报复,清理、打扫战场的任务必须在天亮前完成,他没来得及查询这位战士所在单位及姓名。等到他完成清查战果任务时,烈士遗体已经被打扫战场的同志抬走。从此,烈士的英名便永远消失了。
为这事,郑竹书后悔了一辈子。

原志愿军第50军司令部作战参谋郑竹书
原中国人民志愿军外俘管理处第1团2中队教育中队长苏峥嵘也有一段相关的回忆。他说,英军少校营长柯尼斯进了战俘营后,仍然死要面子不服气:“是你们使用了反坦克炮,打坏了我们的坦克,我才被你们俘虏的。”
苏峥嵘耐心地告诉柯尼斯:“参加那天晚上战斗的我志愿军部队,根本就没有配备反坦克炮,我们炸毁你们坦克的武器是爆破筒、炸药包和手榴弹!”
这话,对绅士般的柯尼斯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奇耻大辱,他几乎跳了起来:“你是吹牛!用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能炸毁我们的重型坦克吗?在我们英国的军事教科书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
注:“皇家重坦克营”,是当晚仅有高中学历的第一四九师政治部敌工组副组长莫若健(其英语老师是着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带着南开毕业的孙崇山担任翻译,捧着《英汉词典》突击审讯200余名战俘时仓促命名的,随即被战地记者李庄、超祺采用,并通过《人民日报》1951年2月26日刊登的《“皇家重坦克营”的覆灭》传开。所以,规范的军史着作在使用“皇家重坦克营”称谓时,都要加上引号。
「赞同、支持、鼓励!」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cwzg.cn/history/201606/2909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