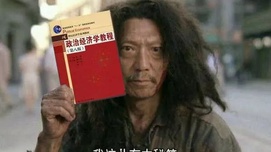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三次转向
本文原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3期
一、引言
自从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大陆确立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如影随形,只是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资本主义危机史。1640年-164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首先把英国带入了资本主义时代。继英国之后,美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等国也进入了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从18世纪30年代起到19世纪下半叶,英、美、法、德、日等国,先后开始并完成了产业革命,迎来了机器大工业及工厂制度建立的新时代,形成了崭新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剩余价值归资本家占有的财富分配制度。实体经济层面的产业革命与制度层面的全面创新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彻底战胜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它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从此,资本主义国家便踏上了迅速发展的快车道。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矛盾的作用,经济危机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
从1825年7月英国爆发第一次周期性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算起,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就从没有终结过。仅19世纪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的危机就包括1837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2年、1882年的6次之多。进入20世纪以后,除1907年、1920年、1937年爆发的局部经济危机外,还有1929年-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1973年的石油危机、1987年和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与过去所发生的多次危机相比较,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新世纪最猛烈、最具有破坏性的总危机。值得深思的是,发达国家每一次费尽心机的制度内调整和每一次积极的与有意识的挽救都为下一次危机埋下更深的隐患。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因此,危机的根源只能从资本的逻辑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寻找,本文就是要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三次转向中来揭示这种寻找的理论脉络。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金融化转向
1.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他们所生活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危机的根源、特征和表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与危害性。马克思认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48页)。在马克思主义看来,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并未超出“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这一范围,至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谓的“监管缺位”“政策失误”“金融创新”之类的说法,其实都是在阐述危机的表面现象,拿这些肤浅理论说明危机的根源,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危机的真正原因(赵磊:《对美国次贷危机根源的反思》,《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1期)。资本主义实践证明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是科学的、正确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资本主义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复杂的变化,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克服自身危机发展的结果。
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经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关系并没有改变,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统治关系也没有改变,但是资本的增值形式却发生了变化: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货币资本是资本价值的主要形式;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的价值形式演变为货币资本和金融资本二元结构。金融产品是最抽象的商品,它不同于其他商品,其区别在于它只有价格而没有价值。因此,金融产品是虚拟产品,金融资本是虚拟资本,金融危机是最深重的危机。
2.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产生机理
与19世纪和20世纪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比较,21世纪初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是内容上更多样、产生机理上更隐蔽、程度上更严重的经济危机。也就是说,实体经济危机在内容、机理、影响范围和程度等方面转向了更深层次的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的产生机理,比过去更深奥。以往的资本主义危机从一开始便可以被人们观察到,从大量商品卖不出去到企业、银行倒闭都历历在目;而现在的资本主义危机则是发生在信贷机构、投资银行、房地产商、贷款人与投资者之间多利益链条下的隐蔽性危机。这个链条的源头是作为信贷机构的银行让不具有资格的申请者获得了信贷,信贷机构将这个存在信贷泡沫的抵押贷款经过处理卖给投资银行,而投资银行对次级抵押贷款进行证券化处理,层层打包成高风险抵押凭证(CDO)之后卖给投资者。当泡沫与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利益链条断裂,危机就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势不可挡。
此次由美国引发的次贷金融危机发生前,信贷机构、投资机构、房地产商等在处理这些高风险金融创新产品时具有隐蔽性、伪装性和欺骗性,使广大普通投资者无法辨别这些金融产品的真假、优劣与好坏。其实,美国华尔街的这些金融大鳄、投资大鳄们十分清楚他们销售的虚拟金融产品是垃圾产品,但是他们却不遗余力地将其销售出去。因为只有这些金融垃圾产品销售出去了,他们才能实现“虚拟剥削”,而这些垃圾金融产品只是他们获得真实利润的工具而已。从过去的“实体经济”危机转向现在的“虚拟金融”危机,从工业剩余价值剥削转向虚拟剩余价值剥削——这是资本主义新阶段的重要特点,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剥削形式转向虚拟化的根本标志。
3.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当资本主义实体经济危机转向金融危机的时候,危机的负面效应就表现为影响程度更深重和影响范围更广泛,即呈现出明显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工业增长如同火车头一样带着资本主义经济向纵深发展,经济危机也主要最先发生在实体工业领域,并由工业领域向金融、商业等领域延伸,经济危机只是在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发生。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工业化需要城市化为其开辟前进的空间,需要金融化为其提供加速发展的催化剂,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往往从占据优势地位的工业领域转移到金融领域,又从金融领域渗透到各个领域,从某一个城市空间蔓延到世界各地的城市空间,从一个国家迅速波及多个国家,特别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此次金融海啸则是影响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这说明此时的经济危机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破坏力。
如果说21世纪之前的危机,只是工业危机、商业危机、生产危机、信用危机的话,那么现阶段的危机则触及包括上述危机在内的政治危机、文化危机、制度危机、生态危机、主权债务危机、次贷危机等诸多方面危机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总危机。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倘若说过去的资本主义危机只影响经济本身的话,那么现在的新经济危机则因政府主权债务危机而影响到政府自身的执政安全,而政府的执政安全是一个国家的核心。这说明以往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病灶”只是在肌体的表层,而今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病灶”已到国家政治的最深层次。
三、金融危机的全球化空间转向
1.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
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全球蔓延时,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回顾资本主义发展史,不难发现,推动全球化的主体是资产阶级。现代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长期发展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产阶级在它取得了统治地位后,把过去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自然的生产关系破坏了,从而建立起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一切时代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资产者的这种不停的动荡,“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然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资产阶级用低价格商品敲开各国各民族的大门,将全球采购原料、全球销售产品、全球布局产业融为一体,把物质文明以及物质文明背后的精神产品一同输出到遥远的异国他乡。“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资产阶级就是通过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复制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复制出资产阶级。事实上,早在世界无产阶级产生之前,世界资产阶级就组成坚强联盟了。现在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为什么不遗余力推动全球化进程,我们所要深入研究的是资产阶级这样做的动力、目的和原因是什么。资产阶级推动全球化的真正动力是资本追逐利润,真正目的是通过不平等交换获得更多剩余价值。有国外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发达国家在国内积累的大量资本需要新的出路,而到不发达国家投资就是为这些资本找到的最好出路。
当资本家的国际投资成为现实之时,马克思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的理论就要在世界范围内审视了(夏振坤:《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评析》,《江汉论坛》1999年第8期)。在世界范围内的利润平均化过程中,大量剩余价值就从不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各国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利润就流向资产阶级手中。为了让这种资金流持续下去,就必须不断地开拓世界市场,将全球化引向深入。在资产阶级将其价值观和大量的资本通过全球化输入世界各地的过程中,空间不平等就出现了,而且这种不平等空间关系还会与不平等交换关系一起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
2.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空意义
资产阶级进行全球化的空间意义就是通过“外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缓解经济危机,其机理就是“以空间换时间”,借此实现资本主义经久不衰的梦想。事实上,全球化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征服世界的手段。在资产阶级征服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屈服”和“集中”两种状态:仅就屈服状态而言,推进全球化的主体与接受全球化的受体之间是不平等的——资产阶级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城乡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东西方之间的屈服关系正是空间上的不平等。可见,转嫁危机的全球化确实导致了空间不平等即空间危机的发生。
资本追逐利润的可持续性是以资本在不同空间的流动性投资为依托的,资本在空间上的作用深度和开拓广度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缓解程度,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就是通过“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办法来暂时性挽救资本主义的。伴随着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空间转向,资本主义也把经济危机带到世界各地。凡资本所到之处,世界性危机爆发之时,无一处空间能躲过危机的辐射范围,这是新世纪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特征。资本的逻辑就是在全球化中将空间异化的同时把时间延续。
3.资本主义空间危机转向的城市化问题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奠基人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列斐伏尔,研究了资本与空间的冲突问题。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指出,空间冲突、空间不公平与空间不平衡都是人为作用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天然形成的,而空间冲突、空间不公平、空间不平衡的制造者正是为了转嫁危机的资产阶级这个群体。另一位新马克思主义者哈维在其着作《资本的界限》《资本的城市化》中强调“城市空间是资本作用的产物”,指出“城市空间的本质是一种建构环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建构环境的生产和创建过程是资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结果”(张应祥、蔡禾:《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述评》,《学术研究》2006年第3期),同时指出“资本主义的城市问题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的空间体现”。当城市被资本征服后,城市冲突就成为空间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
当金融危机转向空间危机时,城市空间的衰落就成为突出问题,美国底特律的衰败就是空间危机在城市层面的实践证明。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资本主义进程对都市空间不断进行重构,而都市化则是资本建立其稳固基础的必然要求”“资本主义城市化的主要动因是资本积累,是资本家受到利益驱使的产物。”(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30页)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通过资本与城市、城市化的联系,才建立起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与空间的联系。发达国家在本国内再塑造或重构城市以及在不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方式重构不发达国家新城市空间的过程日益成为西方国家转嫁经济危机以及金融危机的空间形式。
四、空间危机的制度转向
1.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爆发
空间危机的深化是资本主义制度日益腐朽的表现形式。由于空间的生产是资本生产的载体,资本与空间的后天联系使得空间既是生产的工具,也是消费的工具;既是统治的工具,也是抵抗的工具。而且,空间生产与空间危机正在走向全球化。空间生产的全球化趋势是资本运作的结果,是资本在全球的空间重组,是全球范围内空间生产、城市景观的不断重构。空间因此有了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属性。资本主义的空间是一种生产资料和生产力,能够创造剩余价值,而且是一种消费对象(Henri Lefebvre,TheProductionofSpace,Massachusetts:BlackwellPublishingLtd,1991,p.348.)。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没有灭亡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空间上的无限扩张性和自我突破性,资本主义发现了缓解自己一个世纪以来的内部矛盾的手段:占有并生产空间。”(Henri Lefebvre,TheSurvivalofCapitalism,London:Allison &Busby,1970,pp.70-71.)然而,“占有并生产空间”并不能帮助资本主义制度彻底摆脱矛盾与困境。当各种生产关系不能得到再生产时,最严重的崩溃性资本主义制度危机仍然会到来!
2.资本主义制度的深重罪孽
进入21世纪以来,空间危机的发生为金融危机打上了新时代烙印,这表明空间危机与金融危机的同时发生具有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资产阶级集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最佳空间是城市。城市空间优先发展符合资本追逐利润的逻辑。此时,资产阶级主要是进行“空间中的生产”。由于资本追逐利润的持续与执着,资产阶级创造的生产力已经无法被本国城市空间所容纳时,资产阶级便通过自觉的、主动的全球化扩张战略进行“空间生产”。世界范围内的“空间生产”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一方面,空间已不再是“形式空间”与“实质空间”,而是一种社会性、实践性空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控制之下,空间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一种资本化的商品,是可以进行“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关系。
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疯狂地进行全球化扩张,就是因为他们通过空间形塑、空间成长、空间异化和空间重构不仅可以缓解经济危机,而且还可以为资产阶级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据此,剩余价值生产与分配被国际化了。“空间生产”不仅使剩余价值来源国际化,还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而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不但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扩张开拓广阔领域,也为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的调整留下更广大的回旋余地。“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为了规避环境污染,将其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第三世界,也是一个空间正义的先验性和经验性的问题。”(孔明安:《空间正义的批判及其限度》,《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这样一来,发达国家在获得国际范围内的剩余价值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转移污染而改善了自己国家的生态环境,势必趋之若鹜。这就更加充分地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本质。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就是这种最严重崩溃性危机的表现形式。此次危机与以往历次世界性危机的最大区别在于空间危机与金融危机交织在一起,这种复杂的交织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垂死性。过去,资产阶级通过资本全球化战略来“占有并生产空间”,这种“占有并生产空间”的结果只是暂时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现在,空间特别是城市空间自身也发生了危机,美国占领华尔街抗议行为就是这种源于发达国家的新生代无产阶级在中心城市爆发的城市空间危机的生动体现。这就充分说明了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占有并生产空间”行为只能在一定时期内缓解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演化出的经济危机,而不能最终彻底消除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3.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全球化
如果说以往资本主义工业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还会受到血缘、地缘、民族、宗教、语言等因素的种种阻碍的话,那么,21世纪空间危机转向制度危机时则因新技术的产生可以超越时空到达资本想要去的任何一个地方,资本主义制度危机也随之全球化了。作为资本控制下的空间及“空间生产”必然屈服于资本的统治,而资本所到之处必然会留下异化的脚印,因空间异化、空间冲突等原因而酿成空间危机将不可避免。资本积累的无限性与全球化过程中空间有限性之间存在矛盾,这是发生制度危机的根本原因。全球化是空间的不平衡发展结果,是资本过度积累的恶果,是当代资本主义得以延续的微妙法门(转引自吴宁:《列斐伏尔对空间的政治学反思》,《理论学刊》2008年第5期)。正是资本积累驱使资本家进行全球化扩张,进而驱使空间生产不断发生,但是当空间生产受到空间有限性的限制时,空间危机便胁迫资本危机一同来到人世间。可见,空间的资本主义制度属性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全球化根源。
与资本主义实体工业资本相比,资本主义虚拟资本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实现对不发达国家金融制度的控制,承载着金融风险的虚拟金融资本比工业资本更容易摧毁所有空间壁垒,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不断深化的主要原因。在这里,金融资本的资本主义属性尤为重要,除了具有金融资本的贪婪性、剥削性和扩张性之外,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还具有虚拟性、即时性和超越时空性,在资本主义金融资本超越工业资本优势并且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情况下,金融危机就会转向空间危机,空间危机进而转向制度危机。
在资本主义制度危机逐渐显现的过程中,资本霸权为其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在资本霸权统治下,强势空间与弱势空间之间出现财富分配两极化状况,空间财富结构两极化是引发空间危机的重要原因。当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综合实力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时,该国的资本也就拥有了霸权地位。现阶段,美国就是拥有资本霸权地位的国家,美国因此也就成为输出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强势空间。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之后,虽然美国在全球制造业地位日趋削弱,但美国却开始借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将其金融垄断资本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的弱势空间,而金融垄断资本的贪婪本性与剥削本性又决定了弱势空间的财富必然流向强势空间,使本已贫富悬殊的两个国家空间结构之间不平衡性加剧。可见,强势空间与弱势空间的矛盾正是不同基本社会制度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
五、结论与思考
2007年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来涉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破坏力最强的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是一次最能揭露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罪恶和暴露资本主义运行模式缺陷的总危机,是一次包括商业危机、生产危机、信用危机、能源危机、失业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生态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城市空间危机等多种危机在内的复杂深重的多重性危机。这次危机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具有的科学性,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开辟了深刻认清资本主义本质的崭新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评判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命运铺垫了宏大的时空参照系统。
怎样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就会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这是因为,能够代替资本主义的只有社会主义,而且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中恰恰蕴含了社会主义实践的希望。社会主义实践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它经历了90多年的曲折进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经过74年后失败了,使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但如果从世界向度来看,“苏联的解体不是社会主义事业失败的明证,而是那个僵化模式必改的案例”(杨承训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和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根本缺陷以及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未来趋势。美国的处境为资本主义的命运展示了一幅恐怖画卷,但是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增添了政治魅力,为将来产生具有其他国别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理论提供了生动案例。
面对此次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空间危机,我们的心态不应是幸灾乐祸,而应是冷静深思。当我们看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探究社会主义制度失败与社会主义某种模式失败之间的根本区别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应该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空间危机进行深刻的研究,更应该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质、实践经验及空间生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维度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总结,下一步我们有责任建立具有世界维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依据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空间指向。
参考文献:
[1]王伟光、程恩富、胡乐明:《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上、下),《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7、8期。
[2]王南湜:《剩余价值、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基于改进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3]程恩富:《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求是》2005年第3期。
[4]王志伟:《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
[5]傅德本:《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马克思主义历史回望》(之二),《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6]刘思华:《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7]周延军编着:《西方金融理论》,北京:中信出版社,1996年。
「赞同、支持、鼓励!」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cwzg.cn/theory/201509/246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