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世价值”到“共同价值”:国际话语权的历史转换——兼论两种经济全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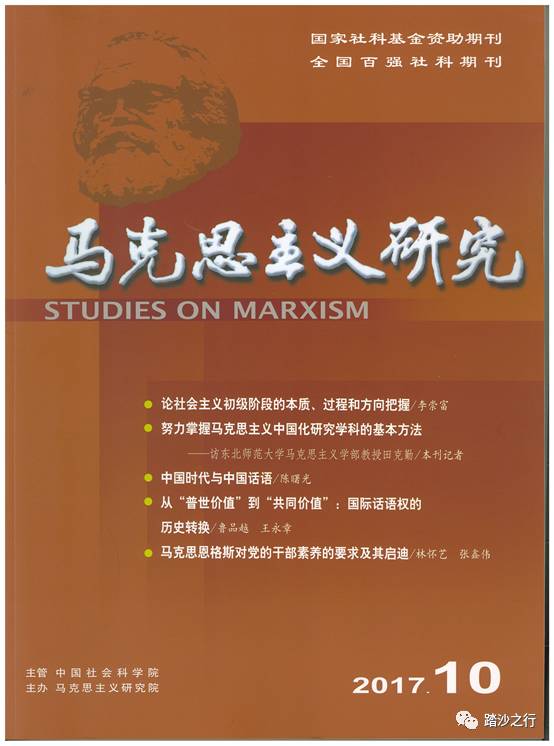
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据着国际话语权的制高点。除了以其强大的科技相军事实力为后盾、以国际传媒体系与文化学术评价体系为阵地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其将推崇的“普世价值”宣扬为“永恒真理与正义”,以站在“人类道德的制高点”自居,并根据由此衍生的“国际标准”来裁判世界各国,干涉别国内政,策动颜色革命,甚至直接用武力颠覆他国政权,建立符合他们意愿的世界秩序。而国内有些学者也认为“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等普世价值”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价值准则,以及由这些准则所规定的基本制度”是“最高文明境界”,是“任何民族最终的制度进化归宿”。可见,中国面临着国际话语权的严峻挑战。是否存在作为“永恒真理与正义”的全人类“普世价值”、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应当如何应对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西方国际话语权的挑战等问题,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普世价值”的理论与世俗来源及其逻辑错误
“普世价值”之所以能够取得国际话语权,不仅仅是因为西方传媒铺天盖地的舆论轰炸,同时也因为它似乎符合人们的常识而容易引起共鸣。这个常识就是:每个人都是人,必然具有与全人类相通的“共性”,而建立在这种“人类共性”基础上的价值必然是“普世价值”。它“与生俱来”,是宇宙永恒真理的体现,是衡量人类社会古往今来的一切制度和一切行为的至高无上的永恒标准,每个社会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正像宇宙万物都必然服从普遍的自然定律一样。于是“否认普世价值就是自绝于人类”,因为“人类”就是由此共性而构成的“类”。因此,一旦站在“普世价值”的立场来发声,就似乎站在了宇宙理性和人类道德的制高点,拥有了至高无上的话语权。
1.“普世价值”的哲学基础:形而上学与神秘主义
上述言论貌似合理,但其立论基础却有着根本性错误。其错误并非承认人类有共性,而是错在对于“社会共性”本质和来源的认识上。产生这种错误的理论路径是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由其导出的“普世价值”可以概括为下述三步曲。
第一步,通过形而上学的“个体抽象法”得到具有抽象共性的抽象个体。由17、18世纪启蒙学者提出的以“自由、平等、人权”为核心的所谓“普世价值”,是关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价值。然而,启蒙学者们却采取以个人为本位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将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向历史进程中的现实的具体个体,从其社会关系中抽取出来,得到马克思所说的“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舍去其个性,抽取其共性,由此得到全人类的“共性”,此即由“个体抽象法”得到的“抽象个体”所具有的“抽象共性”。这种“抽象共性”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由此得到的作为“抽象共性”的人的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是失去现实内容的概念空壳。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和社会契约论将拥有不同地位与财产的现实的人理解为“自由、平等”的抽象“理性经济人”和“政治人”或“法律人”,就都是这样的概念空壳。
第二步,用“抽象个体”构造“抽象社会”。用抽象个人取代处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现实个人,而得到由清一色“抽象个人”组成的“抽象社会”,并以此为理论模型,得到社会交往法则。例如,新古典经济学构造出由平等的、清一色的理性经济人组成的市场杜会;社会契约论将社会理解为由孤立个人组成的抽象社会,其通过投票选举国家机构。这种抽象社会根本不同于现实社会,因为现实存在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在这种“抽象社会”中已经不存在。
第三步,将“人的本性”与“社会规则”赋予神圣色彩而确认为“普世价值”。上述“抽象个人”的共性从何而来?启蒙思想家们将其归结为“天赋”,因而这种由抽象个人组成的“抽象社会”的理性规则,就是天赋的、体现永恒理性与永恒正义的“普世价值”,并以此为标准裁判活生生的现实。至于这种理性与正义如何进入个人与社会之中而得到体现的过程,则是某种先验的神秘过程。正是通过这种神秘主义过程,形而上学者“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的理性相矛盾的东西”。
我们承认,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具有一定认知阶段上的必要性,因为它通过把处于某种默认的联系下的事物的存在状态权且当作事物本身固有的本性,由此可以忽略事物之间的复杂的内在联系,从而简化事物,得到其默认状态下的浅表层次的近似结论。但是,如果将这种简化的方法得到的结论当作一切现实事物的永恒真理及其普世价值,而不深究其默认前提下体现其深层本质的具体真理与具体价值,那就大错特错了。说到底,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人权等,并非“孤立个人”本身所具有的“固有性质”,而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的价值。它们只能在人与人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实践中才能发生,从而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一旦舍去这种现实社会关系而只抓住孤立个人的抽象共性,就舍去了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本身,更谈不上“普世价值”了,所得到的只能是其倡导者默认状态下的价值,而这种“默认状态”正是其倡导者自身所处的世俗基础。
2.“普世价值”的世俗基础:掩藏在“公理”背后的利益关系与价值立场
形而上学者自认为超越了世俗利益,通过“纯理论”的思维程序得到了“普世价值”,因而其“普世价值”乃是消除了一切世俗偏见的“永恒真理与正义”。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实践是人们认识的唯一来源。在上述“普世价值”的理论演绎过程中,其倡导者有意无意地将其所处的社会利益关系与价值立场作为“默认的前提”而设定为“公理”,渗入其理想模型中。不同的理论家倡导的“普世价值”各不相同便是明证。启蒙学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声称自己发现了代表“永恒正义”的“普世价值”,然而二者之间却有天壤之别。在启蒙学者之中,霍布斯、洛克和卢梭都声称自己发现了人的本性、“自然状态”及其“普世价值”,然而其间却大异其趣。美国的《独立宣言》宣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然而当时残酷的奴隶交易却并未因此受到谴责,因为其默认前提是奴隶不属于他们所讲的“人”的范畴。《资本论》深刻地揭露了这些“自由、平等”之类的“天赋人权”的世俗根源:“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古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指边沁的功利主义——引用者注)!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事实上,西方“普世价值”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根基:以抽象的“自由、平等、人权”为“普世价值”的社会契约论是其政治制度的思想根基,以抽象的“理性经济人”为“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则是其经济制度的思想根基。恩格斯早就戳穿了“普世价值”超然于世俗之外的“皇帝的新衣”,指出:“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法国《人权宣言》最后一条写着:私有财产权(核心是资本所有权)“是不可侵犯的与神圣的”,这正是“普世价值”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3.“普世价值”的社会历史后果:抽象“平等”成为现实不平等的放大器
以“普世价值”为根基的抽象社会模型,只是由“抽象个人”组成的虚拟的“抽象社会”,隐去了其世俗根源,从而成为脱离具体内容的形式化体系,由此获得其“普世性”。但这样一来,必然使其成为注定不能实现的乌托邦。在资本主义刚刚走上历吏舞台之际,这种乌托邦理想引导人们从人对人的依赖的封建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促使封建等级制度瓦解,而游离出来的个体则按照这些个人主义价值观进行政治重组与市场重组,由此生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这时“普世价值”的乌托邦理想的确发挥过它的重要历史作用。然而,由此诞生的资本权力却是一种天然的不平等权力——资本家拥有对劳动者的支配权。因而“自由”“平等”的乌托邦必然走向它的反面:由此诞生的是以资本支配劳动为基础的新的不平等的社会。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这种形式上的平等、自由的“普世价值”一旦与具有天然不平等性质的资本权力相结合,所产生的结果只能是“货币平等”与“资本平等”,而不是现实的人与人的“平等”。每个人所拥有的“自由”必然不平等——由其拥有的货币数量来衡量;而其追求个人利益的“机会”与“权利”必然不平等——与其占有的资本力量正相关:人们拥有的资本权力越大,就越有机会和权利扩张自己的财富。在这种经济不平等的基础上形成了人们在受教育机会、政治影响力等方面的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从而产生两极分化。形式上“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由此成为原有的实质不平等的放大器。正如恩格斯所说:“同启豢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这就是现代性困境,凡是奉行“普世价值”的国家,无一不陷入这种现代性困境。
在国际关系上,资本的全球化形成了覆盖全球的国际垄断资本权力系统。今天西方“普世价值”所要瓦解的对象,已经不再是阻碍资本扩张的封建制度,而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国际垄断资本从自身扩张的需要出发,以永远不可能实现的“自由、平等”的乌托邦世界为标准,来评判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力图瓦解其政治经济结构,引诱与威逼其按照西方“普世价值”重建其政治经济制度。当这种抽象的乌托邦模型一旦与发展中国家的各种现实政治经济权力相结合,所产生出来的往往根本不是什么“自由平等的天国”,而是各种社会力量凭借自身所占有的资源“自由”角逐政权的混乱局面,最后只能由国际垄断资本力量来收拾残局,培植顺从国际垄断资本意志的政权和建立相应的社会制度,从而沦为国际垄断资本强国的附庸。“普世价值”由此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力量不平等的放大器,并导致日益两极分化的国际秩序的出现。
4.“普世价值”陷阱:由“国际标准”与“国际范式”引发的民族悲剧
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如果接受“普世价值”,必将陷入永无宁日的困境,因为其不得不继而顺从由“普世价值”衍生而来的“国际标准”与“国际范式”,最后导致整个国家主权丧失,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这就是“普世价值陷阱”。习近平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因为一旦接受“普世价值”,国家将失去统一的政治力量而处于分裂状态,民族纷争与社会动乱此起彼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落干丈,甚至发生内战。此时国际垄断资本力量便趁机强迫我们屈服。“冷战结束以来,在西方价值观念鼓捣下,一些国家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了,有的四分五裂,有的战火纷飞,有的整天乱哄哄的。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这些国家就是典型!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恫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

二、新观念:建立在命运共同体基础上的共同价值
“普世价值”在学理上站不住脚,却在国际话语权上占据统治地位,原因之一是缺乏能够取代它的新观念。习近平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和“共同价值”正是这样的新观念。2013年3月,习近平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深刻地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两年后,他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全世界人民“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是全球最高的国际舞台上首次提出的能够取代“普世价值”的新观念,是与“普世价值”本质上不同的新话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历史性贡献,必将通过人类社会的新实践开创人类历史新时代。
1.社会命运共同体的生成与人类共性的来源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精髓。”我们否认“普世价值”,并非否认人类共性。人类当然具有这个“类”的共性,包括自然共性与社会共性。“普世价值”的错误在干没有搞清楚这种“共性”的真正来源。人类共性并非由“宇宙普遍真理”通过某种神秘途径先验地赋予,不是僵化的永恒不变的“共性”。人类的自然共性由亿万年的生物进化史中的生态关系所形成,而社会共性则由各个层次的社会命运共同体中的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所生成。对这种生成过程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普世价值”的虚妄性,确认“共同价值”的客观性与现实性。
真正的“人性”并非指人的“自然共性”,而是指人的“社会共性”,它决非所谓抽象的“宇宙理性”在个人身上的神秘体现,而是各个不同层次的社会命运共同体的必然的现实产物。个人不可能孤立存在,必须以社会命运共同体的方式集体地生存与发展,由此形成了家庭、村社、民族、政党、国家、国际联合体等各个层次的共同体。马克思曾用“社会人”概念来描述社会命运共同体:“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这里的“社会人”是指由人们的社会关系所结成的有机整体。生活在各个不同层次的社会命运共同体中的人们,彼此利益相连,命运做关,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进而形成“命运共同体”,由此产生了社会命运共同体的性质,如语言文字、文化习俗、伦理准则等,它们渗透于每个社会成员当中,决定了处于同一共同体中的人们之间的“共性”。这些“共性”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现实的产物,产生于社会命运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要。正是基于这些共性的价值评判,形成了该社会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因此,“共同价值”是社会命运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要的产物,而不是抽象的“宇宙理性”的神秘表现。共同价值的主体是相应的社会命运共同体,个人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不断通过社会的交往实践与教化而分享这种共同价值。例如,在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的社会中,形成了关于血缘伦理的共同价值;在以市场为经济纽带的社会中,形成了基于契约伦理的共同价值,因为只有奉行这种契约伦理,市场秩序才能得到维系;在以民族文化为交往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命运共同体(民族)中,形成了民族传统的共同价值。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所说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乃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痛苦的世界各国人民“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联合国宪章》)而确立的共同价值,而非基于“人类本性”的抽象的“普世价值”。
因此,“共同价值”是以各个不同层次的“社会命运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要为基础的价值,各个民族、各个阶级、各个政党等都有其各不相同的共同价值。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全球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形成,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共同价值”也正在生成,这是“共同价值”的最高层次。上述各个层次的“共同价值”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建立在该社会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益与信念基础上的“集体信念共同价值”。每个社会命运共同体都存在着具有共享性的公共利益(如领土、资源等)、共同血缘、民族乃至阶级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该社会命运共同体的其同的符号体系与组织形态(政府、政党等),进而产生了维护这些共同利益的共同价值。它是该社会命运共同体的集体信念与行为准则,是该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的反映,是将该社会命运共同体的成员凝聚在一起的社会关系力量。
其次,是建立在社会命运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补性需要基础上的“契约信用共同价值”。这种客观存在的价值,决非来源于孤立个体的先验的或神赋的“契约精神”的“普世价值”,而是来自于特定的社会命运共同体中人们的社会实践,体现了该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要的共同价值。
在社会分工出现之后,每个人都必须依赖他人而生存,人们之间这种依赖关系形成了互补性利益。例如,市场就是由此产生的自发性“社会命运共同体”,各个区域的经济合作组织(包括国际组织)也是这样的“社会命运共同体”。人们只有共同遵循某种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才能使该社会命运共同体生存与发展下去,由此构成该社会命运共同体的契约性共同价值。
最后,是建立在保障社会命运共同体成员的最基本利益基础上的“行为底线共同价值”。社会命运共同体的成员处于不同的社会生存状态中,成员间的冲突与对抗不可避免,由此可能产生人们之间相互伤害的行为。如果不加制约,就会陌入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之中。为了实现社会命运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对人们的冲突行为进行底线约束,由此产生了关于人们行为的“底线”意识,构成了共同体的“底线性共同价值”。现实的人道主义就体现了这种底线价值。
2.“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本质区别
无论在理论根据、概念内涵,还是历史作用上,以社会命运共同体(其最大者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共同价值”与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普世价值”之间都具有根本性区别,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意义。
首先,二者的世界观基础根本不同。有些学者认为,在各个民族和国家间的各种形式的正常文化交流的语境中,“普世价值”与我们所说的“共同价值”的一致程度就相当高了;而在世界上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民间的文化交流的语境中,“普世价值”与“共同价值”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在西方国家乃至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普罗大众中,“普世价值”已是比较通用的词语了,其内涵就是我们所说的“共同价值”。如果在这种语境中我们硬将这两者对立起来,就不仅会在逻辑上否定了“普世价值”,而且也会在逻辑上否定了“共同价值”。这是一种肤浅而糊涂的观点,其根本缺陷在于未能认识到“普世价值”与“共同价值”在世畀观基础上的本质区别,未能理解什么是“共同价值”。不论在何种“语境”中,“普世价值”的世界观基础都是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是抽象人性论的集中体现,因而是超历史、超社会、超阶级的“永恒价值”。而“共同价值”的世界观基础则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在争取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通过相互交往而形成各个层次的社会命运共同体中的人们的共性,由此产生各个层次的“社会命运共同体”及其“共同价值”。可见,“共同价值”来源于人类的实实在在的交往实践,而不是抽象的神秘的“天理”。
还有些学者认为,我们若在社会交往的语境中反对“普世价值”,就会陷入“孤立”境地,因此我们必须认同“普世价值”。这也是错误的认识。任何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新生事物及其概念,都有一个从少数人坚持逐步发展到被普罗大众接受的历史过程。拿“普世价值”自身来说,它也不是自古就有的观念,而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与发展,随着启蒙思想的教育与鼓吹,而逐渐被西方社会普罗大众所接受的,并进而成为西方垄断资本的国际话语权的社会舆论基础。这种社会舆论基础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存在决定的,也是数百年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刻意塑造的结果。
我们必须改变而不是融入这种“普世价值”的社会舆论之中,新的话语权才能逐步确立起来。这是当今世界的历史发展趋势的客观需要。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日益深重,西方民众对“普世价值”及其衍生的政治经济刹度日益失望。多党轮流执政、政党分肥、政党攻讦造成持续的政局动荡,“三权分立”蜕变为权力掣肘而使政府失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为空中楼阁,正在使西方人民对“普世价值”的信仰发生动摇。因此,用铁的事实揭示“普世价值”概念的虚妄性,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用“共同价值”取而代之,从根本上动摇国际垄断资本拥有话语霸权的舆论环境,重塑国际话语权的群众基础,是当今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在这种历史趋势面前,在社会交往领域把“共同价值”混淆于启蒙思想宣传时的“普世价值”,实际上是用“普世价值”消弭“共同价值”,其结果只能是维护旧的话语霸权的社会基础,进而从根本上维护旧的话语霸权。
其次,二者在内容丰富性上有着本质区别。“普世价值”将建立在“抽象的人的本性”基础上的“自由、平等与人权”作为最高价值,因而其内容与人们的具体处境无关,只是抽象的形式上的自由、平等与人权。而“共同价值”是命运共同体中人们在争取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现实价值,不同层次的命运共同体形成不同的共同价值,它们以其个人和集体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为基础,由此体现于和延伸至经济、政治、伦理、的集体信念价值、契约信用价值与行力底线价值,文化等各个方面,是全面的价值,包括上面所讲其内容的丰富性是“普世价值”所不能比拟的。
最后,二者在社会机制上有着本质区别。“普世价值”被奉为人类唯一正确的价值体系,是一切社会、一切国家都必须无条件服从的价值标准,因而是凌驾于一切社会之上的精神霸权力量。而“共同价值”是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发展的产物,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发展,随着各民族发展道路的不同而多样。每个民族与国家要根据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来形成自身的共同价值,任何民族与国家都不能将自身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今天正处于不断生成的过程中。
贯穿上述这些本质区别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普世价值”立足于抽象个人,并被说成是神秘的“天赋价值”而强加于一切社会和国家,而“共同价值”立足于现实的命运共同体中的社会实践,是各个层面的命运共同体在其追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自我生成的现实利益及其价值。
三、两种价值和两种经济全球化
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升,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也日益频繁与紧密,人类越来越形成相互依赖的命运共同体,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而以“普世价值”与“共同价值”作为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价值理念,必然产生出两种本质不同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

1.“普世价值”推行的经济全球化:以垄断资本扩张为中心的霸权主义经济全球化
以“普世价值”理念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是“国际垄断资本霸权、普世价值话语霸权、强国军事霸权”三位一体的旧经济全球化。
第一,建立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霸权是这种经济全球化的根本目的。国际垄断资本追求自身增殖,必须突破其原有的市场范围而开辟新的扩张空间,由此形成不可遏制的经济全球化扩张冲动。此外,通过经济全球化来分割全球超额剩余价值以滋养自身的社会福利体系,吸收全球生态环境与资源以缓解自身的资源环境危机,这是资本全球化的巨大动力。由此驱动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其目标必然是建立“中心一边缘”世界体系,国际垄断资本及其宗主国是这个体系的权力轴心、金融货币的剩余价值的聚集地,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供应剩余价值与自然资源的边缘地带。
第二,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话语霸权是实现垄断资本霸权的精神工具。这种以“中心一边缘”世界体系为目标状态的经济全球化,必须建立垄断资本运行所需要的刹度环境与文化环境,于是“普世价值”便成为这种经济全球化的开路先锋。垄断资本通过各种学术机构和宣传机器,将上述由抽象个人与抽象社会模型得到的规则描述为天赋的、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普世价值”,作为全人类必须遵循的最高的价值准则,从而获得话语霸权。发展中国家一旦中招接受,掌握这种“普世价值”解释权的西方垄断资本及其政治机构便自然地占据“道义制高点”,取得至高无上的话语权。他们进而根据垄断资本的扩张需要,将抽象的“普世价值”化为一系列具体的“国际标准”,使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彻底丧失,完全听命于国际垄断资本的支配与掌控,这就是“人权高于主权”的真实含义。通过这个过程,“中心一边缘”的世界秩序就一步步沦为霸权主义的世界秩序。而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正是经济全球化中的“普世价值陷阱”的必然结果。
第三,军事霸权成为推进这种经济全球化的最后的强制性物质手段。由国际垄断资本扩张所推行的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引起世界各国人民乃至政府的反抗,其话语霸权也会受到世界各国自身文化的抵制,因此资本霸权与话语霸权的推行最终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早期的经济全球化是通过赤裸裸的坚船利炮的武装殖民活动实现的,其代价惨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经过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国际垄断资本终于发现了一种最廉价的手段,这就是用所谓的“普世价值”来征服人心,作为其武力威胁乃至直接的武装干涉的冠冕堂皇的“正义旗号”。通过铺天盖地的国际舆论工具和教育体系所传播的“普世价值”成为瓦解与祸害发展中国家的一副毒剂,其目的是将世界各国纳入“中心一边缘”的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之中,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其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地与各种危机的最终转嫁地。发生在伊拉克、利比亚、埃及、叙利亚和乌克兰的街头政治与武装冲突便是典型的案例。“普世价值”加上武力威胁推行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局动荡,人民流离失所,并沦为滋生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这样的经济全球化已经越来越难以推行,越来越走上历史的绝路,并导致“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因此,人类必然寻找经济全球化的新观念与新路径,这就是由“共同价值”的新理念推进的经济全球化。

2.共同价值推进的经济全球化:以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
以“共同价值”新理念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价值、各国合作共赢”三位一体的新的经济全球化。
首先,这种新的经济全球化不是由国际垄哳资本扩张冲动与解决危机的需要所驱动的经济全球化,而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人民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相互联系而结成了各个社会、各个地缘单位乃至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在相互依存中形成了利益纽带和内在关联,在共同发展中寻找到了各方利益的交融点和最大公约数。它摈弃了谋求“中心一边缘”国际结构的霸权思维及冷战思维,奉行各国之间“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政策取向,谋求世界各国在互惠互利中实现双赢、多赢和共赢。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形成与遵循在各方相互联系的实践中形成的共同价值。在共同价值基础上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其目的不是将世界各国纳入为某一国家的资本利益服务的体系,而是建立各国共同发展的体系。
其次,这种新的经济全球化不是靠推行“普世价值”以获得至高无上的话语权来维系,而是以共同价值为基础,依靠各国人民平等的话语权来推行。它不是由某个大国或强国集团制定国际规则的经济全球化,而是国与国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在争取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的核心利益的经济全球化。它不是把自己制定的规则强加给其他国家,而是各国通过友好协商来共同制定规则,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经济全球化。这种经济全球化,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向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的原则,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推动不同社会制度互容、不同文化文明互鉴、不同发展模式互惠。各国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合理关切,绝不损人利己、以邻为壑。这种经济全球化致力于世界各国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在经济上深化合作、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在文化上加强交流、增加共识,倡导世界多样性;在安全上加深互信、加强对话,增强合作。
最后,这种新的经济全球化不是依靠武力来推行的经济全球化,而是依靠给各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来推进的经济全球化。我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逐步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建立起物质纽带与精神纽带,从而在扎扎实实的“互联互通”的物质基础上实现经济全球化。它寻求各方利益的聚合点,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具有创新活力的包容性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从而从根本上维护世界和平。它不仅将造福于中国人民,也将造福于沿线各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
这种建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各层次的共同价值基础上的新的经济全球化,将取代以“普世价值”为旗号的旧的经济全球化,成为未来全球化的主沆模式。中国无意成为这种新的经济全球化的领导者,但将成为其忠实的倡导者与实践者。那种认为中国正在取代美国而成为经济全球化规则制定者的观念,混淆了两种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区别,仍是根本上违背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旧的经济全球化观念,需要我们警惕。
参考文献:
[1]陈学明:《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8期。
[2]梁孝:《抽象人性论、“普世价值”和美国的文化战》,《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7期。
[3]徐崇温:《“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辨析》,《学习论坛》2010第7期。
[4]李慎明:《关于民主与普世民主的相关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
[5]侯惠勤:《西方自由主义“普世”理念的破产》,《红旗文稿》2014年第6期。
[6]李崇富:《关于“普世价值”的几点看法》,《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9期。
(作者简介:鲁品越,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永章,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察网www.cwzg.cn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0期,原标题:从“普世价值”到“共同价值”:国际话语权的历史转换——兼论两种经济全球化】
「赞同、支持、鼓励!」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cwzg.cn/theory/201712/3991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