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底线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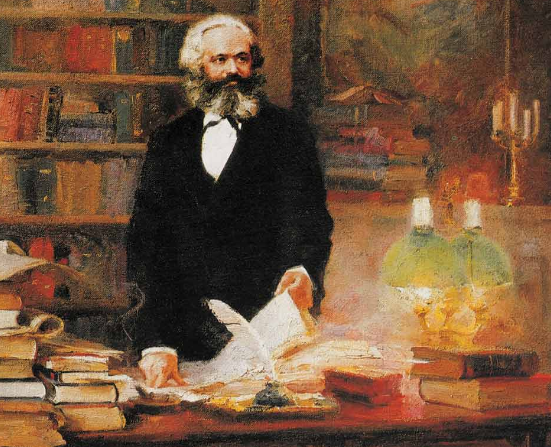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之发生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由问题倒逼而发生的,并非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书斋式研究。这个问题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与中国实际问题之差异。
在逻辑上,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以此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指南,这也就意味着对马克思文本的信奉与遵循。但是,马克思主义是来自欧洲的理论,立足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这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现实之间的间隙。这一间隙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呢?1921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施存统就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出:“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都是拿产业发达的国家底材料做根据的;所以他有些话,不能适用于产业幼稚的国家。……如果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在表面上或者要有与马克思所说的话冲突的地方。”[1](pp.323-324)
毛泽东也曾提出过这一观点,他说自己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着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2](pp.21-22)
施存统和毛泽东的话意味着,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忽视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迟早会出问题。按照胡绳的说法,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有一个艰苦的历程去消化它”。[3](p.45)但是,当时的确有一些人简单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了成功,证明了其真理性,那么,中国人照章办理,也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这样,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凭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俄国经验,开启了革命之路。①
随着革命的深入,中国问题的实际状况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俄国经验之差异慢慢凸显出来。例如,像俄国那样靠攻打城市取得革命的胜利,事实一再证明在中国不可取;像俄国那样强调一切直接依靠工人阶级,也是不可取的,中国是一个农民人数更多的农业国家,没有农民对革命的支持,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形势逼迫之下,革命从城市转移到农村,教条主义也随之而来,即毛泽东所言“洋房子先生”来了。这些人一方面在军事上实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与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跟敌人拼消耗;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实行共产国际的“左”倾关门主义,把所有地主和资产阶级都看成革命的敌人,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拒绝与发动“福建事变”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合作。结果,“到了1934年夏秋之交,中央苏区除了强制性征罚来的粮食暂时尚可支撑外,从武器弹药到食盐、服装等各种物资供应早已陷入绝境,民心也已严重动摇,群众反水和士兵逃亡的现象自1933年夏秋以后就已持续发生。到1934年,已不断出现区委书记、区苏主席、副主席、少共区书记和组织科长等领着群众,成批地带着鸟枪、梭镖等武器反水的情况。8、9两个月,弃械逃归的士兵竟至发展到数千以至上万人之多。显而易见,中央苏区已经再无存在的可能了”。[4](p.340)
由于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实际情况之差异的存在,革命队伍内部就出现了“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争,而且,按照胡乔木1980年的判断,“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同党的集权是互为表里的,因为那是绝对科学,所以你就得绝对服从,这样党内对理论问题就很难讨论了”。[5](p.668)
事实也是如此,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共产国际以及上海的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做法是否算马克思主义,一直表示怀疑,当时流传的说法是“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60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就说,长征前在中央苏区,“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出不了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6](p.504)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中亦证实,“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琪林式的马克思主义者’”,[7](pp.659—660)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应毛泽东的请求,斯大林曾派哲学家尤金对中国进行“学术访问”。1958年7月,毛泽东对尤金说过一段话:“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8](p.388)
问题是,中国革命不是通过理论讨论能够完成的。在1942至1943年批判“左”倾教条主义的笔记中,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9](p.43)
终而,由毛泽东领导而不是“左”倾教条主义者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0](p.500)
深入文献,人们会发现,到193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的言行中已经形成了如下逻辑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基础,无马克思主义则无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中,的确有些内容是无法直接应用于中国实际的;如果强行应用,会给革命带来损失;如果据此放弃马克思主义,那就意味着放弃共产党的事业。因此,在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实际这两者之间,对接的办法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38年1月,持儒家立场的梁漱溟访问延安,他与毛泽东进行了深入交谈。作为局外人,梁氏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表示怀疑,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致命问题发生于外部,而非内部。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并不了解中国社会与欧洲中古、近代社会均非同物,有其特殊构造,只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就造成了中国共产党过去十年劳而无功,仅靠军队维持党的生命。[11](pp.147-148)与梁漱溟交谈之后不久,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2](p.534)②
对此,美国学者斯图尔特·R.施拉姆这样评价:“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的种种概念中,最直率、最大胆地体现了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中国人需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信念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了。”[13](p.55)
二、为什么要提出底线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取得极大成功,为什么还要对其提出底线问题呢?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是实事求是,不能根据文本而要依据事实来形成正确的思路。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是可以改变的,那么,如何确保这种改变不脱离马克思主义立场呢?这就是底线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式提出于1938年,但毛泽东思路的明晰化始于1930年,主要见之于《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恰如标题所言,这篇文章对本本的至上性进行了质疑。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从工作方法出发的,他提出的基本观点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具体阐释为:“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14](p.110)由此引申,错误思路的另一种表现就是“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这就上升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基点问题。毛泽东批评道:“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14](p.111)此处“本本”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拿本本来”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书本所载之观点为工作的出发点。
毛泽东认为,这样的认识和做法不足为据,他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4](pp.111-112)
上述话语深含了思维的革命性意义,所谓“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其深意在于,如果只掌握马克思主义文本,不能付诸实践,甚至相反地用来对付革命事业,那么这种掌握是没有意义的,文本不具备独立的意义和价值;所谓“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当然,这样的工人是不可能掌握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但是,当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来实践马克思主义革命事业时,他们也就将一种“行”转化为“知”——马克思主义的“知”了。完整的表述应该补充一个意思:那些不识字的工人是指被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动员起来的工人——他们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但他们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因此才投身革命事业。这样,毛泽东再一次强调,文本不具备独立的意义和价值,知行必须合一。
在淡化文本的绝对意义和价值以后,毛泽东又提出:“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14](pp.115-116)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形成的思想已经具备了思维方式革命的特征,他否定了从文本原理出发讨论现实的路径,主张从现实出发去验证、补充、修正文本,这样就破除了迷信——不认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就能保证革命的胜利,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证明是对的。1961年9月,英国的蒙哥马利问毛泽东:主席遇到难题的时候,是不是同马克思联系?毛泽东说:他只有理论,他没有办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列宁办过。所以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问苏联。[15](p.28)
这样,“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就完全摆脱了经院哲学的困局,说得上是实现了思维方式的革命。
思维方式的革命发生以后,对毛泽东来说,马克思主义就不再局限于经典着作的文本了,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革命主体对一切客观因素(即世情、国情、党情及其关系)的正确认识和把握。1961年3月,在党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关于调查工作》——作者注)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6](p.567)这一论断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行合一观。
在毛泽东的思维模式里,马克思主义文本上的一切复杂问题迎刃而解,“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当然在乡村尽走尽走,走他几百万年,这也不叫马克思主义,而叫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16](p.332)
纵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人们自然会发现一个现象,尽管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自圆其说地处理了实践与文本之关系,但是,它还得不断地面对如此质疑:当一种理论创新说出了不同于马克思论断的话时,如何才能确保自己还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呢?
对毛泽东而言,早在自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之前,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就已经成为他的思维路径。北伐战争期间,毛泽东就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了农民运动,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于这一着作,美国学者本杰明·I.史华兹就认为:“任何真诚地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都会反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总体的格调——这种格调也明显地反映在当时毛泽东其他着作中。一个一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如何能够接受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创造力的主张?所有陈独秀在其着作中提出来的反对主要依赖农民阶级的不同意见,反映了他自身深刻的偏见,但是这些反对意见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中的老生常谈。”[17](p.69)
史华兹从文本至上的角度断定毛泽东的认识和做法与马克思主义文献是相背离的,这一看法是有代表性的,费正清在1948年就认为,毛泽东的做法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异常(anomaly),这种异常就是“把农民运动作为革命的阶级基础”。他甚至提出,这是中国革命的传统而非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费正清明确提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农民的运动,而非无产阶级的运动。中国遵循的是中国革命传统而不是马克思主义”。③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差异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实内涵,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胜利的真正原因。另一个美国人马思乐说得好:“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论多么背离原初理论的基本假设,对于在一个亟需革命的国度上革命成功,可能有其必要。身处中国的历史环境,一个思想和行动上都恪遵正统马列主义的革命家是不可能成功的。”[18](p.302)
马思乐之说实际上已经触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思想了,一切理论的复杂性都将在实践中予以解决。但是,如果只说“成功就是对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会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化,这里还得讨论革命性思维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前提和底线,就是说,要讨论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基本方面,不妨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真实性底线”,没有这个底线,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了。
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成功实行改革开放,国家面貌日新月异。中国依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党的十九大认为,中国的成功“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19](p.10)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摆脱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之纠缠。在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一方面批评了种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但同时也指出,社会上“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20]回应这样的质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当然就是最大的理论资源,历史就是这么发展而来的,但质疑既然不断出现,也说明底线的讨论还是非常必要的,这涉及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存在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底线何在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实性底线至少有二: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真实性学习与接受;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渗透性存在。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真实性学习与接受”是指,自建党始,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培训自己的干部和普通党员,当然,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条件下,学习培训的程度是有差别的。如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要求高级干部读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五本马列主义经典着作;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要学习12本马列主义着作,即《社会发展史》《共产党宣言》等;1963年,毛泽东又提出学习30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着作的意见。2009年底,党中央批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和《列宁专题文集》(5卷本)出版发行,这两套书被定为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权威性教材。
有一种皮相之论是把这种学习培训看成是形式主义和程序化的——坦率地说,也许有个别干部没有从学习中得到什么,但是,主流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千万不可低估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学习的效果。
现代史学者黄道炫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看资料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国共两党干部写的文章,哪个是共产党写的,哪个是国民党写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共产党的干部比较具有理论判断的色彩,他们会比较重视用联系、辩证的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强烈的理论色彩,从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都很强调辩证法。共产党干部谈的话题,以他们的视野,会把政治、经济、社会、民众的问题打通来看。国民党干部基本上就事论事,很少有放射性的东西,基本上代表中国传统的思路,中国传统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所谓经验理性。”“相对来说,共产党的思想逻辑表现出大得多的辐射力,真的有一些党员了解,通过言传身教灌输,它对党的知行观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越来越深刻,形成党的性格。共产党力量的来源不仅仅是它的组织体系,其实很多时候和它的信仰体系、理论体系是有联系的。”[21]
的确,众多中国共产党干部的文章,处处充满了辩证法、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世界史与中国史视野的交错,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强烈的革命憧憬,而不是像国民党人那样,始终生活在传统文化的精神世界中。蒋介石就是如此,他居然认为日本富强“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窃取了‘致良知’哲学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22](p.535)蒋介石在《革命军人的哲学提要》中论及中日两国,“论土地、文化、人口、历史、道德,无论哪一方面,日本都不足和我们中国比较,但是到了现在却反要受他们的侵略压迫,这是什么道理?就是因为国家失了灵魂”,要想打败日本的侵略,首先就要“恢复整个的中华民族固有的武德——智信仁勇严,继承中华民族一贯的道统”。[23](p.336)
蒋氏的复古主义思路,在国民党要员张治中那里可以得到证实。张治中1948年5月上书蒋介石:“钧座为国家元首、革命党魁,仅持儒家态度以谋治理,似不足完全适应今日之时代。历时愈久,此类抽象之道德观点,一般人民尤其知识分子,甚至党内之若干同志,咸认为老生常谈,不能得到预期之政治效果与良好反应。”④
如果问,复古主义又如何呢?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回忆录中提到美国人韩丁(威廉·辛顿)写的《翻身》,这本书记述了山西张庄被共产党解放以后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黄仁宇说:“书中的一些段落也让我惊觉自己的无动于衷,这是国民党的毛病。问题在于,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亟需立即改革。我们国民党这边的人大可以说:长弓的一切不是我们的错,千百年来向来就是如此,完全是共产党小题大作,以利他们掌权。村民绝不同情我们。只要我们象征‘法治’,就是支持现状,因此就是站在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这一边。”[24](pp.317-318)黄仁宇实际上揭示出了国民党对中国问题持的是复古主义、保守主义思路,而共产党则是持革命的思路、向前看的思路。费正清在国共内战时期亦认为,“蒋介石和陈立夫的新儒家威权主义,不足以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竞争”,后者“但至少比儒家苍白的社会结构理论更为现代化”。⑤费氏当时贬损马克思主义不足为怪,重要的是他认定马克思主义比起国民党的儒家思想来,更适应于现代社会的构建。
当然不是说国民党单纯失败于迷恋儒家思想,而只是说,国民党的思想的确不可能战胜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由于学习与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现代世界的前沿思想,具有了深入而广阔的历史视野,这就是毛泽东所说:“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它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对于社会各个阶级向什么方向发展也看得清楚。比如,我们中国有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中间阶级,我们能看清它们的前途。”[16](p.394)
这里还要提及的一个事实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某些批评我们“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散布一种言论,说什么共产党已经不能直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着作了,怕产生负面影响,云云。⑥但事实是,近年来,在党校和干部学院的培训以及国民教育系列中,马克思主义原着的学习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而且的确是原原本本地学,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中国共产党人的确在学习中提升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某些言论是违背事实真相的,而且严重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着作的理论消化能力。
所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渗透性存在”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导致实践与文本产生差异性存在时,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化形式中可以完全绝迹,反而是必须有所体现,哪怕是一种“渗透性存在”——之所以使用这样一个概念,乃是因为匈牙利卢卡奇有一说法,“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25](pp.47-48)卢卡奇从方法、信念而不是从具体论点来坚守马克思主义,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的,实际上支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路。但是,当卢卡奇说到“新的研究可以完全驳倒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这种新结论”时,我们认为这是过分的说法。很难想象,当马克思每一个个别的论点都被驳倒时,马克思主义还能够存在。因此,我们主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渗透性存在”,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还是可以观察得到的,而不是完全无踪影的。
美国学者史华慈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一书的结论中指出,“除了完全缺乏共产主义政党和工业无产阶级的有机联系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保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的基本要素”。史华慈认定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第一个原理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历史救赎过程的信仰,列宁对共产党是历史救赎的唯一代表的信仰”。第二个原理是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与实践。史华慈认为:“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和实践得到了坚持,一个反映人民群众急切愿望和要求的,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组织严密而富有活力的党组织,在确保革命成功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第三个原理是列宁主义固有的集权主义倾向。史华慈认为,中国继承了这一倾向,并提出“这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核心要素之一”。第四个原理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史华慈认为:“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原理,曾极大地吸引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这种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联系起来,也使中国知识分子找到了自己的角色”。[26](pp.185-186)可以说,这就是对“渗透性存在”的确认。
1959年2月,毛泽东同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进行了谈话。马特说:“列宁说专政只能由一个政党执行,而主席先生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由几个政党联合执行,这是不是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的回答是:“不能说离开了马列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中国有两次革命:一九四九年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问题,那时我们没有触动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后一次革命,想必你也知道,就触及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以及个体手工业与个体农业的所有制。对这些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几个步骤。后一次革命经过几年,已基本完成。这两次革命,都是以共产党为领导进行的。”[8](p.3)
毛泽东所论,就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中国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如果说,多党合作的设计与马克思、列宁的主张有距离的话,那么,毛泽东认为,当多党合作的体制是由共产党而不是别的党来领导时,那就克服了表面的距离并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这可以理解为“渗透性存在”之含义。应该说,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今天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所有的理论要点都可以分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渗透性存在”。因此,对于那些怀疑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我们一方面有着来自实践层面的自信,另一方面也有着源于文本深层次构成分析的自信。
本文系上海市2017年度“建国70周年”研究系列:“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历程与经验教训研究”[2017BHB0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在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张闻天说,当时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这些错误在反五次“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博古说,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王稼祥说,我也是实际工作经验很少,同样在莫斯科学了一些理论。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196页。
②晋察冀日报社编的1944年版《毛泽东选集》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一句刊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③转引自路克利:《国际显学与批判思潮——国际毛主义研究六十年》,《文史哲》2014年第4期。
④转引自黄道炫,陈铁健:《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
⑤转引自路克利:《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7页。
⑥2015年的互联网上有一则信息,由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散布,他说自己在上海书城相遇一位阅读《共产党宣言》的农民工,农民工说读了以后,意识到这个社会必须要修理了,修理不了就要推倒重来就要革命,要革命就一定要读《共产党宣言》。“年轻人的一席话,让经历过惊涛骇浪、堪称老资格政治家的戚本禹惊讶莫名、一时失语”。参见何清涟等:《中国:溃而不崩》,台北:八旗文化/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276页。
参考文献:
[1]林代照,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
[2]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金冲及.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4]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7][苏]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M].张岱云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8]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杨奎松.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美]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典藏版)[M].田松年,杨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6]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7][美]本杰明·I.史华兹.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
[M].陈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8][美]马思乐.毛主义的诞生:中国共产党革命之路[M].温洽溢译.台北:卫城出版社,2012.
[1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21]王奇生与黄道炫对话:研究中共党史必须具有全球史眼光[N].北京青年报,2015-03-20.
[22]蒋介石.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M].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4.
[23]蒋介石.庐山训练集[M].南京:新中国出版社,1947.
[24][美]黄仁宇.黄河青山[M].北京:三联书店,2001.
[25][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6][美]本杰明·I.史华兹.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M].陈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黄力之,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察网(www.cwzg.cn)摘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5期】
「赞同、支持、鼓励!」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