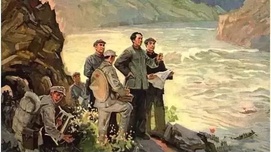杨玉:构建中国特色的历史自我意识和自主的历史叙事

论历史评价尺度释义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关于历史进步性评价,马克思主义坚持二重尺度说——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总的来说,历史尺度对应生产力水平提高,价值尺度则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两者在历史的长河中实现动态统一。但是,若选择历史横切面静态观之,似乎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评价的结果往往是相悖的,这就引起了两种尺度何者具有优先性的争论。其实,无论认为“历史尺度优先”还是“价值尺度优先”,都是对马克思历史评价尺度理论的错误解读,都在逻辑上隐含着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历史虚无主义者片面解读历史、歪曲历史人物、否认历史规律客观性,意图歪曲颠覆重大历史问题,对这种错误思潮必须进行批判和抵制。
一、历史评价尺度“优先论”的片面性及其历史虚无主义表征
1.“历史尺度优先”观点的错误与批判
认为马克思主张“历史尺度优先”的观点主要根据马克思早年对于英国殖民印度的评价。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与《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结果》中,曾指出西方殖民国家对东方国家的种种血腥罪行,他们视东方人民的性命为草芥,疯狂进行残暴屠杀。从价值尺度看,这种行为毫无疑问应当被强烈谴责。但同时马克思文章中也描述了东方社会原始的一面:东方社会相互独立的农村公社限制了人们的活动范围,地域之间实现不了广泛的交往;封闭的生存环境使人们产生强烈的奴性,渐渐丧失敢于突破与创新的精神,正是这种落后的状态给了殖民侵略者可乘之机。从历史尺度来看,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使多年来阻碍东方社会发展的传统社会结构分崩离析,可以说是给东方国家带来了一场革命,客观上起到了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马克思还指出,“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2]有学者从这段话中解读出,如果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产生分歧,马克思主张“历史尺度优先”。理由是: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发生冲突的根源,在于生产力的不发达,只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才能化解这一冲突,实现二者的统一。“这就说明,在社会现象的历史意义与价值意义中,历史意义具有最终的发言权;在社会进步评价的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中,历史尺度居于更基础的地位。”[3]“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历史评价始终是首要的,价值评价则是第二位的。”[4]
上述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误解了马克思的本意,不自觉地滑入了历史虚无主义泥潭中,因为“历史尺度优先”观点确认了殖民侵略有功,从逻辑上等于否定了反殖民侵略斗争的历史意义。事实上确实有人把马克思这个论断——“殖民侵略充当不自觉革命工具”作为所谓马克思主张“历史尺度优先”原则的理由。如果按照这个原则重新书写中国近代史,结果会如何呢?当时日本的现代化水平比中国高很多,也就意味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也能够“充当不自觉革命工具”;既然殖民侵略有功,要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那么,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就没有任何历史进步意义了。这符合马克思的主张吗?
首先,马克思确实强调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侵略肩负着“破坏与重建”的双重使命,但这不是确认马克思主张“历史尺度优先”原则的理由,因为马克思同时也指出了,印度只有取得民族独立才能取得真正的历史进步。“历史尺度优先”观点往往忽略了这个因素。“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5]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的“历史尺度优先”——英国给印度带来现代工业化,只是为印度自身的历史进步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印度人民要想真正获得历史进步,还需要一个类似“价值尺度优先”性质的前提条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另外还需要明确的是,马克思对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评价只是个例,其中的观点并不完全适用于其他殖民统治中。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被殖民侵略的情况不同,即使是同一殖民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进行殖民侵略的目的也会有区别,不能一概而论、以点概面。仅根据马克思关于英国殖民印度的评论就得出“历史尺度优先”的结论是不妥当的,由此结论推演出落后国家无需进行反殖民侵略斗争更是对马克思极大的误解,很明显是犯了片面解读历史的错误,带有明显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2.“价值尺度优先”观点的错误与批判
认为马克思主张“价值尺度优先”的观点多见于对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解读中,尤其是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释义。马克思在研究俄国社会问题时,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认为俄国公社在一定条件下,“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6]进入社会主义。有学者认为,将“跨越”理论与马克思早年关于英国殖民印度的论述比较,很容易发现马克思历史评价尺度重心之转移,“这是马克思晚年对人的价值理想的空前的提升,跨越‘卡夫丁峡谷’既是‘价值评价优先’,又实现了历史的巨大进步,是‘价值评价优先’与历史评价相统一的体现”[7]。“价值尺度优先”的观点在逻辑上否定了生产力对历史进步的决定作用,违背了唯物史观基本原则,难免陷入“人道主义历史观”,即使不滑入历史虚无主义窠臼,也会为历史虚无主义侵蚀留下缺口,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攻击的目标。
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最早见于文献是马克思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之后出现于1881年3月《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期间三年多时间,正是马克思写作《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时候。因此,正确解读“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对这两部着作的研究十分重要。毋庸置疑,《人类学笔记》是马克思晚年重要的理论着作,所述理论也看似与他早年的一些观点背道而驰,学术界有些成果甚至将《人类学笔记》里关于东方社会的论述称为马克思“晚年的困惑”,认为马克思以往评价历史进步的尺度是生产力发展,但现在“人道主义在这里已经不仅是伦理规范,而且已经成为马克思规划历史的尺度和出发点了”。[8]但是将《人类学笔记》跟马克思晚年的另一着作——《历史学笔记》结合研究会发现,马克思晚年有一个研究重心的转移,不过这个转移并不是将评价历史的尺度提升到人道主义,马克思晚年的研究重点依然是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
人道主义包含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伦理观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历史观是人对于历史问题的观点,包括历史规律、本质等方面。如果人道主义也是一种历史观,就必然会对人类历史有独特见解。人道主义历史观重视人类生存状况的改善,提倡人类个性自由与自身价值的实现,但往往过于感性,没有把人放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作理性的分析,这与唯物史观背道而驰,因而必然导致唯心主义历史观。社会发展的全部历程就是社会形态从低到高不断演变,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国家或民族出现发展停滞或跨越等现象,都取决于这个国家或民族当时的历史环境、生产力状况和世界交往的程度。“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正是指落后国家由于自身特殊具体历史环境,可以通过世界交往的方式,吸收其他国家的积极优秀成果来发展自身的生产力,从而过渡到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由此看来,“跨越”理论依然遵循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依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与关照之下,而不是人道主义原则。“如果历史观是人道主义的,无论其言辞多么诚恳,多么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多么富有人性和情感,但对现实问题只会得出错误的结论。”[9]
马克思晚年历史评价尺度的重点确实发生了转换,他着重强调了历史评价的价值尺度,认为西方的殖民统治不仅破坏了东方社会原来的结构,而且对东方社会没有进步作用。这种转换的原因在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发展形势的判断会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1853年马克思着英国侵略印度的文章之际,适值资本主义发展昌盛,加之此前欧洲革命败北,使他觉得当时革命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而晚年提出“跨越”理论时,资本主义种种弊端已经暴露,欧美各国遭受致命危机。另外,马克思一直认为西方国家在落后国家实行殖民掠夺,会让资本主义在这些地方生根发芽,属于新生力量,有巨大的潜力,届时即便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也很有可能被这些刚踏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镇压下去。“大陆上革命已经迫在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广大得多的地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10]所以马克思晚年劝告俄国等前资本主义国家不必着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应该把土地公有制保留下来作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是马克思晚年对价值尺度侧重未曾使他放弃运用历史尺度。《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里,马克思分析了俄国社会经济的特殊环境,论述了俄国农村公社原始以及落后状态,并结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指出,俄国社会想要向前发展就要打破目前孤立的状态,马克思在此就是用历史尺度评价俄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因此,将马克思的思想作整体分析就会发现,他关于历史评价尺度重心的转移是和历史规律相统一的。然而,恰恰有学者“截取”了马克思晚年关于历史评价尺度的重点转换这一点,片面主张在历史评价中应该坚持“价值尺度优先”原则,这无疑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肢解”。承认“跨越”理论体现“价值尺度优先”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对“跨越”理论的关照,是对我国“跨越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光辉历史的虚无。
二、马克思历史评价尺度学说的思想演变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一生中不同的时期分别将历史评价理论的二重尺度提到了“优先”的位置,马克思对历史的评价是“从‘历史评价优先’转到‘价值评价优先’”[11]。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道德尺度优先”的典范,而马克思对历史的评价则是“从‘道德评价优先’转换到‘历史评价优先’”[12]。“至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际,马克思的批判视角实现了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之深刻转化,届时,基于‘历史评价优先’视角的历史批评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范式中居于强势地位。”[13]那么,马克思历史评价尺度学说究竟是怎样演变的呢?
1.马克思历史评价尺度学说的基本背景及最初酝酿
在1845年以前,由于深受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仍然是一个人本主义思想家,不论是在莱茵报时期还是在德法年鉴时期,他的着作都有着明显的人本主义色彩,尤其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探讨的宗教异化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过渡,这本着作里马克思首次从经济角度关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工人的劳动异化问题,认为异化劳动是人本质的丧失,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色彩,是马克思价值评判的起点。同时马克思又指出理想劳动是人类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无疑是为历史评价的价值尺度注入了客观的物质内容,包含着历史尺度的内核。由此可见,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是同源而生的。
2.马克思历史评价尺度学说在原则上的确立:唯物史观的奠基
19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马克思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从道德层面和价值层面对工人阶级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及其异化现象进行考察,而是侧重从历史尺度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行逻辑论证和经济学验证。从《神圣家族》开始,马克思给予历史尺度以独立的地位,把“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看作“历史的发源地”,剔除了劳动范畴中的理想成分,《神圣家族》可以说是全面批判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前哨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把物质资料的生产看作第一位并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确立了历史尺度在历史评价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表标志着唯物史观的确立,马克思逐渐意识到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历史尺度在衡量社会进步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14]唯物史观的立场是对唯心史观的批判,改变了以往历史评价领域中“人道主义历史观”泛滥的现象,彻底批驳了德国理论家们“观念的历史”。唯物史观的确立奠基了历史评价学说的原则,即二重尺度辩证统一。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这是马克思从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不同方面对历史进步加以评价的结果。《哲学的贫困》虽然是一部驳论,然而它在批判蒲鲁东主要观点的同时,辉煌地论证和阐述了马克思历史评价学说的基本方法——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持辩证的看法,即使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肮脏的,它吸噬了无数人的鲜血,但是资产阶级在历史上也起过进步革命的作用。他们反对以道德感伤主义的论调来看待资产阶级,而是拨开呈现出来的美好景象,从社会底层和工人阶级的角度,从全部人类社会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客观看待异化状态的资本主义及其各阶级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也是从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的层面来评价社会进步的。
3.马克思历史评价尺度学说的全面建立和运用
19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进步评价尺度思想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成熟并应用于实践。马克思在晚年人类学研究期间,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有机统一。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重重,弊病展露无遗。同时,事实表明落后国家根本无法依靠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走上发展道路。基于此,马克思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认为俄国不必经历资本主义残酷剥削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既符合了历史发展规律,又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的关怀。
三、坚持历史评价二重尺度的辩证统一
事实上,无论认为马克思主张哪个尺度优先都是认为历史评价的二重尺度存在悖论。“二重尺度悖论”观念是教条式解读马克思思想造成的,它违反了唯物史观的辩证法精神。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是并列而非从属关系,是一对相互独立又有共同指向的范畴,无论认为哪一个尺度具有优先性都是对另一尺度独立性的忽视。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也并非“不可能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具备‘合题’条件”[15]。二者在实践的推动下,在“现实的人”身上、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着动态统一。
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从产生根源上看分别对应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持“历史尺度优先”观点的学者似乎将历史规律视为一种外化于人的客观力量,这种力量不受人的控制反而支配着人的主观选择。事实上,唯物史观虽然认为历史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这里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不是将历史规律看作“人之外”的神秘力量,“它虽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却是以人的实践能力和认知能力的发展水平为转移的”,这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程度,是以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能力的发展程度为转移的,是随着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能力和与之相应的认识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减弱的”[16]。也就是说,历史规律既包括对主体实践的客观限定性,也强调主体的能动选择性,主体的能动选择如果顺应了客观规律即会促进社会发展,反之则会导致发展滞后甚至倒退。因此,随着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实践活动会越来越自发地顺应客观规律,越来越降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程度。可见,将历史规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部分理解为置身于人之外的客观力量,是对唯物史观的严重误解,而由此得出的“历史尺度对价值尺度具有优先性”的结论也与唯物史观背道而驰。
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从实践上看分别对应生产力进步与人的发展。也许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生产力进步不但不会促进人的发展,反而会带来人性堕落、道德沦丧。例如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从历史尺度来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从价值尺度看这种过渡却包含着人性的堕落与倒退。正如恩格斯所说:“它是被那种使人感到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退化,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17]种种类似的现象使得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二者看似相互矛盾,但纵观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生产力的进步与人的发展总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没有生产力的进步,人的活动就会受限,达不到全面发展所必需的普遍交往;没有人的发展,人在从事物质资料生产中就会失去积极性,不利于生产力的进步。
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不管在什么历史阶段,人的价值诉求中总有不被生产力认可的内容,但是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实践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使先前不被生产力认可的那部分诉求得到满足,而这部分被现实化了的价值诉求就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即实现了理想式的价值尺度到现实式的历史尺度的转变。由此看来,历史尺度并不是外在于人的需求、外在于价值尺度的,它是在人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将价值尺度现实化而逐步构建起来的。人们就是这样在价值尺度的引导下把自己的价值诉求变为现实,不断丰富历史尺度的内涵。价值尺度与历史尺度中互相矛盾的内核也将会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彻底消逝,共产主义社会将使所有主体的价值尺度实现统一,也会使人们的价值尺度与历史尺度实现统一。
历史尺度以现实生产力发展为依据,哪怕牺牲部分人的利益;而价值尺度以现实的人的发展为评判标准,却难免含有些许理想化的内核。两种尺度既有各自合理之处,也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在评价历史的过程中,二者要相互补充、结合,协同发挥作用。若是过度重视价值尺度中某些不被生产力认可的想法,容易导致理想化;若是忽视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类的价值追求,而单纯地将生产力发展作为唯一标准衡量历史发展,容易导致形而上学的独断论。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有着统一的理想境界,若只用静止眼光看待社会发展,就会对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关系作绝对化解读。
四、揭示历史评价尺度释义中存在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意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评价尺度学说的解读是一个传统问题,但即使一个司空见惯的老问题,也未必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藏身之所。当我们深入研究一些学者对该学说的释义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一些释义也隐含着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反思。因此,揭示历史评价尺度释义中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它不仅能够增强唯物史观的理论批判功能和历史解释功能,有效抵制唯物史观错误解读中的负面影响,而且有助于正确评价历史,构建中国特色的历史自我意识和自主的历史叙事。
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立足的根基,正确评价我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历史不仅能够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对于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也具有重要意义。若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全面地、辩证地分析历史,其实就是给历史虚无主义借题发挥的机会。因此,在评价我国近代历史的过程中,要坚持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辩证统一的原则,防止对历史的曲解。
有学者在评价我国近代历史的时候,坚持“历史尺度优先”观点,把殖民侵略与“近代文明”等同起来,由此得出“殖民有功”的结论,认为“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甚至慨叹“中国要康乐富强,先得被殖民150年不为过”,这些观点是何等荒谬。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进行殖民统治的目的可谓是司马昭之心,他们为了自身的发展,怎会允许这些廉价原料及劳动力的来源地独立起来,走上现代化呢?“殖民有功”的看法忽略了马克思晚年对殖民侵略的谴责,无视殖民主义者对落后国家的残酷掠夺,是对被压迫国家反侵略斗争英勇历史的虚无。
还有学者认为,我国虽然“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种跨越是在“价值尺度优先”观点的关照之下的,只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并不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因此中国应当倒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历史虚无主义认为,五四以来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方向是偏离文明主流和走上歧路;认为“斯大林和晚年毛泽东搞的那个穷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8],甚至将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成就认定为“向资本主义文明的回归”。“所谓历史虚无主义,说到底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19]历史虚无主义者企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较低生产力基础之上建立的,不是“正统”的社会主义。这种观点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只能适应比资本主义更好的生产力,而低于这个生产力水平的国家无法建设社会主义,是生产力原则教条论,是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光辉历史之虚无。
中国已经进入了经济飞速发展的新时代,但社会新矛盾的出现,文化多元化的交织,以及西方意识形态的入侵,使人们在社会评价尺度问题上的观点异常混乱。一些学者错误地解读马克思历史尺度评价的理论,违背唯物史观的根本精神,导致对历史的种种错误评价,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传播泛滥。揭示马克思主义论断释义中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科学性、解释力,才能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提供有力的理论保障。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5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62页。
[3]邢立军、章文雯:《论社会进步及其评价尺度》,《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4]丰子义:《关于历史进步的评价问题》,《学术月刊》2007年第12期。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6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8页。
[7]张奎良:《作为“历史之谜”的异化及其评价尺度——与俞吾金先生切磋》,《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8]张奎良:《马克思晚年的困惑》,《光明日报》1989年5月29日。
[9]施九青:《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是人道主义历史观的争论——关于评价经济制度先进落后的生产力标准与价值标准》,《改革与战略》2013年第9期。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11]张奎良:《作为“历史之谜”的异化及其评价尺度——与俞吾金先生切磋》,《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12]俞吾金:《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13]余京华:《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历史唯物主义之创立是否消解了道德批判?》,《伦理学研究》2014年第1期。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3页。
[15]龚培河、万丽华:《“价值尺度服从历史尺度”是一个真命题吗?》,《长白学刊》2008年第6期。
[16]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18]谢韬、辛子陵:《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19]龚书铎:《历史虚无主义二题》,《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5期。
【杨玉,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原载《世界社主义研究》2018年第九期,授权察网发布】
「赞同、支持、鼓励!」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