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彭德怀信件认识拐点的国际背景
摘要:1959年庐山会议前夕,苏共中央突然决定中断提供核武器资料样品与彭德怀路过莫斯科时间的某些契合,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7月14日信件与赫鲁晓夫反对人民公社言论的某些契合,引起了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高度警惕。庐山会议硝烟扩大到适与赫鲁晓夫有公务接触的彭德怀身上,构成了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对彭德怀信件认识拐点的重大国际背景,构成为错误批判彭德怀的重要可能成因之一。
关键词:毛泽东;赫鲁晓夫;彭德怀信件;庐山会议
毛泽东去世以后,学术界探讨1959年庐山会议文论较多,主要围绕着彭德怀7月14日“意见书”及纠“左”反右、背景成因,比较详尽地探讨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错误发动对彭德怀批判之原因。研究1959年庐山会议,不能仅仅局限于研究毛泽东与彭德怀个人的分和,忽略这段历史衍变的国际因素。本文试图由此切入,回归1959年庐山会议重大国际背景,梳理与探讨中共中央在庐山会议前夕收到苏共中央中断核武器样品的信件及赫鲁晓夫同期在阿尔巴尼亚和波兰的某些言论。这些事件与彭德怀7月14日给毛泽东信件主要倾向的某些“吻合”,促发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相关时论及行径“内外结合”的高度警惕,由此可能导致了对彭德怀7月14日信件的认识拐点及错误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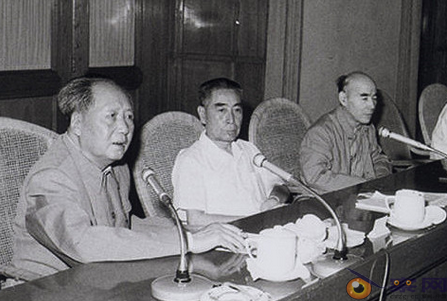
一
1959年乃多事之秋。1月27日,苏共二十一大召开,两大重要信息引起全世界高度关注:一是苏共提出排除世界战争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二是“大会意识形态论述中对公社问题的阐述表明,莫斯科间接地对北平进行了指责”,美国国务院情报局迅速捕捉到这一“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变化[1],加快了对中国的围堵。同年3月5日,美国续与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八国等签订共同防御协定[2]后,再与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分别签订双边军事协定[3],进一步加剧了对新中国的战略合围。3月17日,达赖及随员在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后出逃,在外部势力唆使帮助下,于3月31日逃至印占区,当即被同意“政治避难”[4],印度总理尼赫鲁旋多次发表要求西藏独立的讲话。4月23日,赫鲁晓夫写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主张在空间停止一切核试验。5月15日,赫鲁晓夫再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信,信中写道:“您对我今年4月23日的信的复信收到了。苏联政府对美国政府的声明表示满意。……苏联政府一向希望永远地和普遍地禁止试验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这是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的。苏联政府确信,根据上述考虑,将能够找到解决办法,来排除我们之间的分歧,并在最近期间达成协议。”[5]同一天,赫鲁晓夫以同样的内容向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复信[6]。
赫鲁晓夫这番对美、英的表态包含着众多的中国元素。按照1957年10月15日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应在1959年6月如期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相关技术资料。6月8日,赫鲁晓夫千呼万唤的“苏、美、英三国关于停止核试验会议在日内瓦开始举行”[7]。6月20日,苏共中央通过了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信中提出“为不影响苏、美、英首脑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日内瓦会议的谈判,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暂缓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料”,待两年后,“彻底澄清西方国家对于禁止试验核武器问题以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态度”时,再决定提供与否。苏联认为,这样做不会影响中国的研制,因为“中国生产出裂变物质至少还要两年,到时才需要核武器的技术资料”[8]。苏共中央这封信不仅堂而皇之单方面“腰斩”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同时极为强势地释放了赫鲁晓夫靠拢美英,遏制或打压新中国研制核武器之势。对于这一点,美国国务院情报和研究署早在1959年3月27日报告中就判断了苏联不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资料。因为“北平获得核武器将使莫斯科孜孜以求的苏联在裁军领域的目标进一步复杂化。此外,莫斯科将从根本上对北平拥有核武器是否是明智之举产生严重怀疑”[9]。
1959年6月26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苏达可夫向周恩来递交了苏共中央这封信。[10]《周恩来年谱》同日记载了周恩来接见苏联专家,就大跃进发表讲话:“中国搞大跃进的目的是为了迫切需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担负起我们在社会主义阵营应当担负的任务,大跃进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是发展的速度,第二是平衡,第三是质量。我们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11]周恩来这个讲话与毛泽东的相关思考完全一致。“6月27日,周恩来到医院看望陈毅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后离京”[12]。此时周恩来当确知苏共中央6月20日来信内容。《周恩来年谱》记载:1959年6月28日,周恩来到达武昌,用电话与毛泽东商定庐山会议讨论的问题,作了补充[13]。这个补充,应该包括刚刚了解的苏共中央来信内容的汇报。所以,7月1日毛泽东上庐山后,对原计划讨论的问题两次作增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十八、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十九、国际问题”[14]。“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15]。毛泽东将对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认识,特别放在国际问题讨论中,这表示了毛泽东早已知道苏联对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有些看法,联系到6月20日苏共中央来信,他特别意味深长地讲“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时间才看得出来的”,字里行间流露着某些苦衷与警惕。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不讲原则”或“信用”的警惕由来已久。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反对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共产主义再也不是原来的形象了。为人们得知好几十年来在人民的名义下曾有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后,开始对这个制度,而不仅是对斯大林主义产生了极大的怀疑”[16]。据美国蒙特克莱尔大学格雷弗教授的新近考证,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谈斯大林的61条罪状,其中60条均为不确或诬陷[17]。可见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带来的负面和不实阴影。赫鲁晓夫在苏共党内的颠覆能力早已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1957年6月,赫鲁晓夫利用苏国防部长朱可夫的军队势力,将苏共中央主席团中斯大林分子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网诺维奇打成反党集团。同年10月26日,又将亲信马利诺夫斯基取代尾大不掉的朱可夫任国防部长。1958年3月,赫鲁晓夫逼迫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尔辞职,自兼其职。一个月后,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给我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提出希望中苏两国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电台[18]。1958年7月,又发生了苏联大使尤金转告赫鲁晓夫希望中苏建立联合舰队之事,毛泽东7月22日与尤金谈话,一针见血质疑:“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在这个(联合舰队)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但其他方面的合作还可以进行,决不会闹翻。我们还是始终一致地支持苏联。我们可以在房子里吵架”[19]。毛泽东此时已深刻洞悉苏联投石问路,企图将中国国防逐渐纳入苏联指挥棒下的某些迹象。故毫不含糊地表达了既要维护中苏友谊,又要高度警惕苏联以合作之名的各种控制。
二
在这种情况下,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以将与美、英签订停止一切核试验协定之由,不予提供原已与中国签约的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这种变相遏制打压中国研制核试验的政治行径,促使中共中央要不束手就缚,甘当附庸卫星国,要不自力更生,针锋相对。1959年7月上旬,庐山会议召开期间,中共中央高层已开会决定自己搞原子弹。《周恩来年谱》记载了“向宋任穷等传达中央关于研制核武器方面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20]。从会议进程推算,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1959年7月14日前应该知道这件事[21]。关于这一点,当事人之一的宋任穷,1994年出版的回忆录可为佐证。其曰:“1959年7月4日,我根据党组讨论的情况,给聂老总写信,向他报告了我们对苏方来信的分析,并提出三个对策方案……聂老总说,等庐山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让我、刘杰、万毅三人到庐山向他和彭老总汇报。会议预定7月14日结束,让我们7月14日到。……我们在庐山期间,关于苏共中央来信和我们分析研究的情况,我向彭老总和聂老总作了汇报,彭老总由于在受批判”[22],“听完我们的汇报后,没有讲什么意见。聂老总说,苏联不给,我们就自己搞。我说,我们一方面自己搞,一方面要说他们不履行合同,继续向他们要。当时我还带了一份由刘杰亲笔起草代中央拟的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在向周总理汇报时,请示周总理要不要
复信,总理说,中央研究了,我们不理他那一套,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23]。按照正常程序,聂荣臻在庐山会议上收到宋任穷1959年7月4日来信,当向国防部长彭德怀汇报主要内容。而且宋任穷上山时,彭德怀尚没有受到批判。7月18日以后,毛泽东才将彭德怀7月14日信公开。7月23日,毛泽东才发表大会讲话。
针对苏共中央6月20日信件,中共中央决定自己搞原子弹,这在庐山会议上是不断发酵的大事。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他曾提到庐山上传达过苏联中断提供核武器样品那封信,大家很气愤,对中央决定勒紧裤腰带自己搞原子弹,非常拥护。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问题的认识变化,严格说起来,也是与苏共中央这封信及赫鲁晓夫的相关言论,赫鲁晓夫与彭德怀的某些接触颇有联系[24]。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59年6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听取彭德怀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波兰等八个国家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彭真、黄克诚出席。”[25]《毛泽东年谱》中注明是八个国家。但当年报刊对外宣传也是“以彭德怀元帅为首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应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7个国家国防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军事公安部的邀请,前往上述各国进行友好访问。”[26]然而,实际上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履经九个国家,包括前苏联。1959年4月24日,以彭德怀为团长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开始东欧之行,团员有王树声、萧华、张宗逊、杨得志、陈伯钧、张学思、陈熙、路扬、朱开印、郑文翰、冯征。第一站波兰,第二站东德,随后军事代表团访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5月28日,中国军事代表团到达阿尔巴尼亚,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亦于5月25日已先达,6月5日离开,中苏两国代表团在地拉那不期而遇。5月29日下午,彭德怀出席苏联驻阿尔巴尼亚大使为赫鲁晓夫举行的招待会,5月30日下午参加地拉那中心广场欢迎赫鲁晓夫大会,彭德怀被邀请坐在主席台赫鲁晓夫的旁边,晚上,彭德怀出席了阿方招待赫鲁晓夫宴会。在阿尔巴尼亚,彭德怀客观上多次与赫鲁晓夫相遇接触。6月6日,赫鲁晓夫访问阿尔巴尼亚归国后,在莫斯科群众欢迎大会上讲话,特别提到:“苏联党政代表团在阿尔巴尼亚访问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也飞抵那里进行友好访问,因此我们也同他进行了愉快的会面和交谈。”[27]赫鲁晓夫这段讲话特别强调“愉快”二字。另,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行程,当年所有报纸仅写前往东欧7国和归程经蒙古访问,均未提到苏联,故至今多种版本“共和国大事记”均未记载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经过苏联履经九国一事,连《毛泽东年谱》中也记载是八国。当然,也可能莫斯科作为往返途径国,没有正式访问任务,故未记载。但是不能回避彭德怀在莫斯科确实与赫鲁晓夫有公务接触。据驻苏大使刘晓回忆:1959年,彭德怀路过莫斯科时,在机场上向迎接他的苏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表示,要与赫鲁晓夫会见。彭德怀要见赫鲁晓夫,主要是为了把建设中国军事工业的一些重要项目落实下来,这件事只有赫鲁晓夫才能做决定。因此,当彭德怀访七国回莫的第二天,赫鲁晓夫接见了彭德怀。彭德怀和赫鲁晓夫会见前,我先到赫鲁晓夫的秘书办公室等候。苏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传达,赫鲁晓夫的这次谈话主要是交换中苏两国军事上共同有关的问题,参加会议的苏方人员有安东诺夫大将。赫鲁晓夫除强调苏联核武器、新式武器的威力以及苏联海、陆、空军现代化装备与力量强大外,特别提到为防备美在远东侵略,尤其是对中国的军事侵略。苏联在远东地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和空军力量,一旦有事可以对中国进行强大的援助。赫鲁晓夫说美国对中国进行军事冒险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因此赫鲁晓夫向彭德怀提出,中苏两国进行具体军事合作有迫切的必要,特别是要迅速安排中苏海军与空军的合作。这方面是美国的强处,是中国目前的弱处,如海军与空军方面能实现合作,这一形势就会改变。赫鲁晓夫又表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可以以苏联为中心和华沙条约国军事条约衔接起来,这也就是华沙主军事条约的延伸。彭德怀表示可以向中央请示,研究赫鲁晓夫的想法,这从战略方面来看对中国是会有帮助的。至于合作的具体方案和形式,他回国研究后,再与苏方共同研究。彭德怀接着向赫鲁晓夫提出要求加强对中国军事装备与新式军事技术的援助。在说到这个问题时,彭德怀向赫鲁晓夫说明了我国国防计划方面要加强的地方,我国当时军队的编制与军事装备和急需的装备革新及补充等情况。赫鲁晓夫听后,对彭德怀的要求均表示原则同意,提出在军事装备与技术援助时要多派专家来帮助我国,并希望中国武器生产与苏联统一化,彭德怀表示请示中央考虑。此外,也谈到了一些有关南斯拉夫、裁军、四国首脑会议以及当时苏联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争论问题。[28]
刘晓(1908-1988)是1926年入党的老员,参加过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党的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中央续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1955年至1962年任驻苏大使。1959年8月参加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这段他亲历的1959年6月初彭德怀与赫鲁晓夫的接触应该是当年他作为驻苏大使和中央委员,庐山会议前和党的八届十中庐山会议时必须向中央汇报的高度秘密性重要内容。这些内容也应该包括当年米高扬等对彭德怀的赞扬。刘晓回忆:在彭德怀访问七个东欧国家将回莫斯科前,我在外交场合活动中遇见了米高扬,米向我说,苏联方面高度评价彭德怀这次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访问,其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
他说彭德怀会了解这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经验教训,他们如何运用苏联的经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苏联为中心加强团结互助合作,交流经验,统一步调是非常重要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最可靠的保证,也可以加快速度向共产主义迈进。关于这些,中国也会如此
理解。他希望,彭将这次访问的结果向中国介绍,将会使中国对各社会主义国家迫切需要互助合作、统一步调的愿望能进一步了解。各社会主义国家也希望中国在这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与发展的一个强大的因素。他希望我将他的这些意见转告彭德怀。当彭总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我就把米高扬的话全部转告了彭总[29]。
米高扬要求转达给彭德怀的这一段话重点就是一句:社会主义各国要统一步调,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中国对统一步调进一步了解。这就是当时苏联、东欧、亚洲各国执政的共产党都知道的赫鲁晓夫的一句“名言”,叫“对对表”[30]。
刘晓1962年从驻苏大使回国后,续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1967年至1968年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其后被迫害身陷囹圄七年。他对彭德怀1959年访苏回忆,是在彭德怀彻底平反后公开发表的,可以排除文过饰非的主观动机。刘晓的这个回忆表明,1959年庐山会议的所谓彭德怀“里通外国”,可能是整个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的重要拐点。
三
彭德怀生前关于1959年6月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的这段接触,在《彭德怀自述》“庐山会议前后”一章中,仅写了一句话“我在一九五九年五月访问了东欧各国,六月中旬回到北京”[31]。如此的简略或回避,并不符合彭德怀坦荡耿直之个性,也不符合个人自传详略得当的基本要求。对照《彭德怀自述》编辑组1981年为该书写的“出版说明”特别强调的,“在整理时,我们以一九七0年的自传式材料为基础,以其他几份材料做补充,相互参照,统一划分了章节,对文字衔接和标点做了一些技术性的整理;对部分内容作了删节。此外,均保持原貌”[32]。《彭德怀自述》是1970年撰写的所谓“检讨交代材料”,应该有1959年5-6月访东欧各国的内容,但随着1978年12月对彭德怀的彻底平反,这部分相关文字是不是属于该书删节的“部分内容”呢?这似乎从另一个角度反证了刘晓那段回忆的某种可信性。
公允地说,彭德怀1959年5月在阿尔巴尼亚和赫鲁晓夫有过公务接触,1959年6月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有过交谈,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庐山会议上了解诸种情况后的印象应该是深刻的超强的。一是1958年苏联国防部是通过彭德怀转达,坚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1958年7月21日、7月22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连续与尤金会谈,彭德怀均在座,毛泽东鲜明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33]7月31日,赫鲁晓夫特为此事来中国,四次会谈彭德怀亦在座。赫鲁晓夫表示永远不会提军事“合作社”这样的问题。但赫鲁晓夫在1959年6月彭德怀停留莫斯科期间,对彭德怀强调“苏联在远东地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和空军力量,一旦有事可以对中国进行强大的援助。赫说美国对中国进行军事冒险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因此赫鲁晓夫向彭德怀提出,中苏两进行具体军事合作有迫切的必要,特别是要迅速安排中苏海军与空军的合作”[34]。赫鲁晓夫显然食言了,打破了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底线;二是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苏共高层多次策动颠覆政敌活动;三是苏联对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执政党高层多次蛊惑颠覆“第一把手”;四是彭德怀回国当月,苏联恰恰违约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五是赫鲁晓夫在国际上大肆宣传与彭德怀“愉快的会面和交谈”。这一切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特别是在不断收到苏联释放的非议“大跃进”、“人民公社”之声时,必然加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及苏联国防部“对对表”的警惕,包括当年与他们有公务接触的彭德怀的警惕,就当时而言,这应该是一个主权国家难以避免的。亦是毛泽东对彭德怀7月14日信件认识逐渐复杂化的重要拐点之所在。
关于中苏两党关系,1959年10月15日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署研究报告有过分析:
在当前中苏关系中,也许最持久和基本的刺激物是莫斯科一直对中共的国内计划———人民公社不赞成。在十周年庆祝活动中,中共对意识形态正统学说和人民公社的可行性的有力扞卫达到了顶点,持续时间达1个月。期间,莫斯科继续公开贬低人民公社,北平暗示苏联对人民公社消极的观点在中共国内的争论中也起了作用。从时间上看,这个新的对公社批评,几乎与北平对中共内部的人民公社计划反对者的揭露同时发生,反对者引用了苏联立场,企图以此加强他们的立场[35]。
苏联不赞同中国的人民公社,美国人分析有三个深层次原因,一是恐惧中国更加强烈地要求试验核武器,二是恐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第二个意识形态中心出现,三是寄希望于中国党内部亲苏力量的出现[36]。1959年米高扬请刘晓带话彭德怀都从某些侧面反映了这一倾向。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针对彭德怀7月14日信件大会讲话,其实最关键的最警惕的也是这种倾向。正如毛泽东在那次讲话中所说,“为什么郑州会议不提,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不提”,是不是言下之意彭德怀与赫鲁晓夫1959年5、6月多次见面后才提?这是1959年庐山会议重大国际背景错综复杂之焦点,也是毛泽东等误判彭德怀等人的重要可能历史成因。
(责任编辑:马纯红)
注释:
[1]沈志华、杨奎松:《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5册,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350页。
[2]卫林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0页。
[3]卫林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9页。
[4]《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139页;西藏自治区政协文
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册,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86-87页。
[5]《赫鲁晓夫言论》第12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出版,第88-90页。
[6]《赫鲁晓夫言论》第12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出版,第91-92页。
[7]卫林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页。
[8]沈志华、杨奎松:《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5册,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352页。
[9]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237页。
[1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页。
[1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页。
[1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页。
[1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页。
[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1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6-87页。
[16][美]塔德·舒尔茨:《昨与今———战后世界的变迁》,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页。
[17]2014年10月格雷弗在第五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发表的论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几个问题》。
[18]卫林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页。
[19]《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
[2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41页。
[21]《聂荣臻年谱》(下),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680页。“7月上旬,审阅宋任穷4日由北京写来的报
告,……阅后嘱秘书告宋任穷等,等庐山会议快结束时,请他与刘杰、万毅于14日来庐山汇报。”据此,收
到宋任穷报告的7月上旬,聂荣臻按照中共逐级汇报制度,当及时向国防部长彭德怀作了汇报。
[22]《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351页。“7月15日,宋任穷、刘杰、万毅到达庐山,
随即听取他们汇报。7月16日下午,(聂荣臻)同彭德怀一起听取宋任穷、刘杰、万毅关于对苏联共产党
中央6月20日致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信的看法和意见的汇报”。
[23]《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353页。
[24]资料为2007年7月7日,笔者在北京玉渊南路陶鲁笳家中采访其所谈。
[2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26]戴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
[27]《赫鲁晓夫言论》第12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206页。
[28]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110页。
[29]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111页。
[30]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111页。
[3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66页。
[32]《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页。
[33]《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
[34]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
[35]沈志华、杨奎松:《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5册,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373页。
[36]沈志华、杨奎松:《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5册,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379-403页。
【作者:马社香,女,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江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研究员。基金项目: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开放项目(项目编号:2015y6),本文原载于《毛泽东研究》】
「赞同、支持、鼓励!」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cwzg.cn/history/201612/3334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