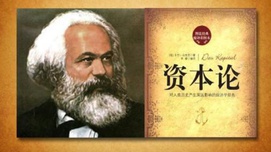《资本论》:一部关于人的解放的伟大学说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独家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微信公众号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一、《资本论》就是一部关于人的解放学说的伟大巨着
马克思的思想尽管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其核心主题就是一个,这就是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这一核心思想体现在他的全部着述和实践活动中,自然也体现在他的主要着作《资本论》中。《资本论》说到底,就是一部关于人的解放学说的伟大巨着。它关注人,关心人,以人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以人的解放为根本目的。马克思指出:“我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①]由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我们这里所涉及的人,就是或首先指是工人阶级。为此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研究了工人阶级当时的现状、未来发展、历史使命,以及工人阶级解放的一般前提与具体条件等。并且,它还为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这就是贯穿其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以及运用这一方法严格论证和详细阐述的劳动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工人阶级,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最伟大的阶级,它不仅肩负着解放自己的历史重任,而且还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责任与使命,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论》又是实实在在的一部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马克思指出:人的解放,即社会的解放,它“是通过工人阶级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 [②]
是否关注人,关心人,以实现人的解放为根本目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一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所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从来就是只研究物或财富,研究它们的生产、增长与分配,但就是不研究人,尤其是不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所以,那些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只是资产阶级的一门“完整的致富的科学”。同时,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政治经济学还是一门“非人的学问”。因为他们虽然也非常看重劳动,并“把劳动提高为国民经济学的唯一原则”,然而,他们却从来不关心“在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的人”。不仅如此,他们还“把人当作商品,当作商品人,当作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甚至只被“当作精神上和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③] 或 “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④] 据此,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敌视人的”,它是资产阶级“犬儒主义”的经济学。[⑤]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是一种“天然的”和“永恒的自然形式”。[⑥] 由此,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分工也是“天然的”、“永恒的”,所以,工人阶级今天的现状如何,未来的命运怎样,一切都是用不着关心的。关心了反而会伤害上天的意志。至于现代的西方经济学家,在本质上同他们的先辈一样,也是为资产阶级效忠与服务的。不过,由于现代工人阶级队伍的成熟与觉悟,资本家再也不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靠残酷的剥削来致富,也不能靠残酷的专制来统治,因而,他们也十分关注人,研究人。于是,所谓“资本民主”、“工人自治”、“收入均等”等奇谈怪论纷纷出笼,并且不断花样翻新,蛊惑人心。因此,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除了是一部关于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学问”外,同时还是一部为资产阶级发财致富进行辩护的伪科学。
因此,是否关注人,关心人,以实现人的解放为根本目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一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所在。《资本论》就是一部关于人的解放的伟大学说。
二、《资本论》关于人的解放的主要内容
什么是人的解放?它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包含有哪些内容?这是《资本论》及其一系列手稿首先为我们回答的问题。马克思指出:人的解放,就是人的本质的复归,或是“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⑦]当然,“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或人的本质的复归,并不是要人回到它的原生态,而是要它回到自己应该具有的那种本质规定性上来,回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上来。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它是人的“自由和自觉的活动。”所谓自由,即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⑧] 因而,它是人对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真正主体的体现,而不受来自自然、社会,乃至自身等方面的限制或强制。而自觉,就是人的活动的主动性、目的性、能动性体现,不存在任何的盲目性与被动性。可见,人的解放,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使人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当然,人的解放,首先还是要把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各种异化现象、受剥削和遭奴役的非人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在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不把工人当人看,仅仅把他们当作会劳动的动物,否认人的社会属性及其丰富的内涵,所以,马克思关注工人阶级的状况,关心他们的命运,关注他们的未来。在中学时代,他在考虑自己未来职业选择时,决意要选择“为人类的幸福”和“同时代人的完美”而奋斗。他的这种崇高选择都全部倾注到了自己的理论创作与社会实践活动当中。他的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更是如此。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决意要把工人阶级从以下几个方面解放出来。
第一,从旧的社会分工中解放出来。
社会分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上曾有过几次,每一次新的社会分工的出现都对社会经济及各个方面的发展起到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又在许多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城乡对立和对劳动者自身发展的影响等方面。马克思指出:“就劳动过程是纯粹个人的劳动过程来说,同一劳动者是把后来彼此分离开来的一切职能结合在一起的。当他为了自己的生活目的对自然物实行占有时,他是自己支配自己的。后来他成为被支配者。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后来它们分离开来,直到处于敌对的对立状态。”[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与对立,不仅发生在和存在于企业中,而且还发生在和存在于社会上,并且带来了城乡之间的分离与对立。马克思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与对立。“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农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⑩]
不论是企业内的分工,还是社会上的分工,在私有制、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劳动者自身的发展总是不利的。马克思指出:在城乡对立的情况下,“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11] 在企业内的情况更是如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工场内部把社会上现存的工场手工业的自然分离再生产出来,并系统地把它发展到极端,从而在实际上生产出局部工人的技艺。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把局部劳动变为一个人的终生职业,”[12]使之“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变成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 [13]这种情况到了大机器生产阶段,又有了新的变化与大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大工业从技术上消灭了那种使整个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的工场手工业分工。但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同时又更可怕地再生产出了这种分工”, 结果把工人变成了局部机器的仅仅有自我意识的附件而已。[14]
第二,从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本来应该是人的一种“自由和自觉的活动”,它是人所特有的创造物质财富的生动实践。然而,在私有制、尤其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被异化了,走到了它的反面。它变成了“一种不自由的”,“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强制和压制下的活动。”[15]首先,在劳动过程与劳动者之间发生了异化。劳动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它是人的脑力与体力的自由运用与发展,因而也是人的自身价值的实现过程。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它就是人的一种特殊的享受。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却变成了完全相反的另一回事。它变成了“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了,他要“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劳动。[16]其次,在劳动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之间发生了异化。劳动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它是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实现其对自然物的占有的过程。这其中,劳动者是这一过程的主体或主观因素,而劳动资料总是它的客体或客观因素。劳动资料是一种无生命、无意识的死的东西,是劳动者实现其物质变换的手段和工具。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其情形却完全反过来了。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如机器,而是机器使用工人。马克思指出:“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因此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 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17]这是一种荒唐的颠倒。另外,在劳动产品与劳动者之间发生了异化。众所周知,劳动产品本来就是劳动者创造的,理应为劳动者所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却只为资本家所有,而工人始终只能作为雇用劳动者而存在。
异化劳动是私有制的特殊产物,也是它的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却表现得更隐蔽。它是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所谓公平交易的基础上实现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它是以“商品生产所有权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权规律”来表现的。他指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既然每一次交易都始终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资本家总是购买劳动力,工人总是出卖劳动力,甚至还可以假定这种交易是按劳动力的实际价值进行的;那么很明显,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表现为最初行为的等价物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别人的活劳动。”他还指出:“起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现在,所有权对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18]
第三,从资本主义雇用奴隶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指出:“一个除自己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19]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这般。不过,他们并不像罗马的奴隶那样是由锁链,而是由一种看不见的线即雇用劳动这种关系系在资本家的手里的。由于雇用劳动这种关系的存在,决定了工人不仅终生、而且世代都必须像赫斐斯塔司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一样被永久地钉在了资本的柱子上,永远为资本家所有。马克思指出:“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但是,起初仅仅是起点的东西后来通过过程的简单连续,即通过简单再生产,就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结果而不断重新生产出来,并且永久化了。一方面,生产过程不断地把物质财富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资本家的价值增殖手段和消费品。另一方面工人不断地像进入生产过程时那样又走出这个过程——财富的人身源泉,但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因为他在进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占有,并入资本中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物化在别人产品中。”[20]另外,工人的个人消费也是从属于资本的,他们的吃、喝,“正像给蒸汽机添媒加水,给机轮上油一样”。因此,他们的个人消费,在资本家看来也是一种直接的生产消费。[21]
工人对资本的这种关系,还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技术因素的进步与变化而不断地将其从形式上的隶属转变为实质上的隶属,越来越紧地将工人拴在资本的柱子上,使工人终生、乃至世代任资本宰割。
第四,从资本主义的过度劳动和饥饿中解放出来。
过度劳动,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因为资本主义对剩余劳动的占有是通过剩余价值这种形式来实现的。这较之以往通过使用价值来实现对剩余劳动的占有的其他社会来说,显得更贪婪、更残酷。马克思指出:“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但是很明显,如果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不过,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灾祸之上,再加上一层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22]因为赚钱或生产剩余价值是这个社会生产的绝对规律。作为资本家,不过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机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23]为此,他肆无忌惮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使之“不仅超过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24]到最后,不得不由政府立法予以强行干预,把工作日限定在一个为工人勉强能够接受的界限内。
过度劳动不仅剥夺了工人“身体上的正常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且还使他们“未老先衰和死亡”。[25]即使是那些有幸活下来的人,也只能在失业与饥饿中度过。这种情况,随着资本积累的累进进行,变得越来越糟糕。马克思指出:“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越大。……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在法文版中为‘成正比’。笔者注)。最后,工人阶级中贫困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26]这表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不仅要经受过度劳动的折磨,而且还要忍受贫困与饥饿的折磨。
第五,从旧社会所造成的思想贫乏与愚昧中解放出来。
人是万物之灵。它充满智慧,富于创造。它不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而且还创造了绚丽多姿的精神财富。但是,工人,由于资本主义的精神侵害和强加于他们的过度劳动,不仅失去了智力发展的生理基础,而且也剥夺了智力发展的物质条件与社会环境。因为资本主义旧的劳动分工把工人终生拴在机器上,变成了机器的简单附属物,不仅使工人的劳动变得单调乏味,毫无内容,而且使他们失去了广泛的社会接触,严重“侵吞了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 [27]损坏了他们地神经系统。另外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还造成了“智力与体力劳动相分离”与对立,使工人而失去了思想灵感。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力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从而在工人一极造成了“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8]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真实情况的写照。
第六,从资本主义旧的意识形态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并且每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9]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不仅在经济上是资产阶级的奴隶,接受它的奴役,而且在精神上也是它的奴隶,接受它的奴役。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在经济上的利益和政治上的统治,除了运用暴力的力量外,还运用意识形态的力量来为自己服务。如他们广泛散布所谓资本主义制度是“天然的”、“永恒的”,他们和工人之间的“分工”也是“自然的”、“合理的”等种种胡言乱语;又如,他们大肆贩卖什么在他们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是“自由的”、“平等的”,同工人的交换也是尊重工人劳动力的“所有权”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等货色;再如,他们鼓吹他们并没有剥削工人,不是工人养活了他们,而是他们养活了工人,他们之所以越来越富是因为他们能“节欲”,或是为工人的劳动提供了“服务”所得的报酬多,或是自己的劳动“创造”了更大的价值等论调,如此等等。 此外,他们还利用一些御用文人,捏造一些奇怪的理论来为自己服务。如一些形形色色的价值理论、利润理论、拜物教理论(包括各种形式的宗教)等等。这些理论千奇百怪、五花八门,但其共同特点就是诋毁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千方百计地为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作辩护。他们把价值、利润、利息、企业主收入、地租等都说成是资本家的资本(如机器、厂房、土地乃至其他自然物等)自行增殖的结果,极力掩盖它的真实来源,以蒙蔽工人耳目。
此外,人的解放,还包括使人从自然和社会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因为在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还不十分发达的条件下,在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和掌握它们的发展变化规律的情况下,人的一切实践活动不免总会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与被动性。当人的行为违背了这些客观规律的时候,他们就会受到来自自然或社会方面的种种惩罚和报复。只要这种情况还存在,人的解放总还会有一定的路程要走。因此,人的解放也还要包括这方面的内容。
综上所述,可见,上述种种现象都是同人,具体说就是同工人的人的本质相对立的,是对人的本质的根本背离与否定。只有把人从这种同人的本质相对立或背离与否定中解放出来,才能使人实现向“人的本质的回归”,或达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关于人的解放的真实内容。
三、《资本论》关于人的解放的一般前提和具体条件
上述分析,使我们看到,人的本质的种种异化都是资本主义对人的剥削与奴役的结果。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人的本质的异化,工人阶级就一定摆脱不了“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的命运。因此,工人阶级要想实现自己的解放,就必须推翻整个资产阶级及其整个社会制度。马克思指出:“逃亡奴隶仅仅是力求自由地发展和巩固他们现有的生存条件,因而归根到底只是力求达到自由劳动;而无产者,为了保存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至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旧社会生存的条件,即消灭劳动(根据本书第68页注2的解释,这里的“劳动”是指“现代形式”的劳动,即资本主义的雇用劳动。笔者注)。”[30]推翻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要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因而,只有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即“自由人的联合体”,[31]它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2]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推翻和立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并不能立即实现人的真正解放(或彻底解放),它只是为实现人的解放提供了一个一般的前提。因为此时的共产主义还只是它的开始,一个发展的起点,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或它的初级阶段,它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33]因此,要实现人的真正解放,还必须经过一个长时期的发展,为其创造一系列的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具体条件。
如前所述,人的真正解放,必须是人的全部发展,因此,人的真正解放的条件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对此,在《资本论》及其有关着作中,马克思作了具体阐述。
第一,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马克思始终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个致命的东西,“它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34]不仅如此,它还决定着劳动者的命运。资本主义制度给工人命运造成的全部罪孽就在于资产阶级掌握了全部生产资料,而工人却没有。因此,在社会主义阶段,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了这一要害问题。马克思告诫人们:当无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以后,必须“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地剥夺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以此作为社会确立的根本前提。[35]
当然,仅仅具有这样一个条件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为联合的条件。”[36]这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全部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才能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以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将得以消失,进而使那种迫使人们奴隶般的分工也将归于消失;有了这个基础,才能使劳动失去谋生手段的性质而变为人的一种精神享受与追求。有了这样的基础,才能为人的真正解放或全面发展提供充裕的物质条件和奠定良好的精神文化基础。
第二,发展和普及教育,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与能力,促进劳动的自由变换。
要实现人的解放,必须发展和普及教育,以促进劳动的自由变换。马克思指出:“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种规律的正常实现。……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为此,他还指出:“工艺学校和农业学校是这种变革过程在大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职业学校是另一个要素,……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37]另外,他还十分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认为这“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办法。”[38]马克思在这里所阐述的一些基本原则不仅适用于职业教育,而且也是适用于其他所有形式的教育的。只有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劳动才能实现自由变换。反过来,劳动的自由变换又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必须把发展和普及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人的素质与能力的提高,还包括人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的提高。有了这种能力的提高,才能使人在自然和社会面前获得“自由自觉的活动”可能,真正实现向人的本质的复归。因此,发展和普及教育,不仅要教给人们一些应有的科学文化(包括思想道德)知识,还要教给他们一些科学的思想方法,既提高他们的文化道德水平,也提高他们的认识能力。
第三,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人的发展提供充分的自由活动时间。
人的解放和发展,离不开充分的自由活动时间。如果没有这种时间,人们想接受教育、从事社交、发展和运用智力等一切都不可能。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人的自由活动时间。他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发展的空间。”[39]他还指出:“如果把资本创造的生产力的发展也考虑在内,那么,社会在6小时内将生产出必要的丰富产品,这6小时生产的将比现在12小时生产的还多,同时所有的人都会有6小时‘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40]为此,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另外,马克思还认为,为了使全社会成员都获得更多的自由活动时间,还应当尽量减少社会的非生产人员,消除有闲者阶层,实现平等劳动与平等享受。只有这样,才能为人的发展提供充裕的自由活动时间。
第四,同旧的社会意识形态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旧的社会意识形态,是旧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他们服务的思想工具,也是禁闭大众的精神枷锁,如我们在前文所谈到的资产阶级的种种奇谈怪论和荒唐理论就是如此。只要他们还存在一天,就一天也谈不上思想解放,人的解放。所以,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革命,不仅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还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41]所以,他在《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的所有奇谈怪论和荒唐理论都一一作了无情的批判与抨击。他的这些批判,不仅为人的解放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也为人的解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四、简短的结语
《资本论》是一部完整的关于人的解放学说的伟大巨着。它详细分析了工人阶级的当前状况、未来发展、历史使命及其获得解放的一般前提与具体条件等等,构成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学说的理论体系。在这里,不论马克思所提供的方法论,还是他确定的一系列科学原理,尽管与我们当今的社会相去100多年,但是,它的基本原理、科学精髓仍然是有效的,是指导我们今天的行动指南。尽管我们今天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马克思提出的关于人的解放的历史任务并没有真正解决,甚至还有很大的距离。近年来,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构想,就其精神实质来说,就是为了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我们今天乃至今后所要做的一切都没有超出马克思当年的预想。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仍然是指导我们今天践行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指导思想。它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注释:
[①]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
[②] 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1
[③] 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7
[④] 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5
[⑤] 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3
[⑥]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8
[⑦] 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1
[⑧] 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0
[⑨]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55-556
[⑩]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47.
[11]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47.
[12]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77
[13]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76
[14]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31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9
[16]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09-210
[17]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63-464
[18]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39-640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5.
[20]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26
[21]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27
[22]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63-264
[23]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60
[24]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95
[25]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95
[26]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95
[27]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63
[28]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64
[29]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42
[30]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77
[31]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5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0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0
[34]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 94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72
[36]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69
[37]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4-535
[38]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0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32
[40] 马克思 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81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1-272
【屈炳祥,察网专栏学者,武汉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系《资本论》与市场经济。本文原载《经济学家》2007年第6期,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赞同、支持、鼓励!」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cwzg.cn/theory/201811/455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