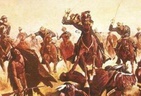田辰山:新时代中国道路是一条生态哲学道路——一个平白易懂看世界方法
【本文为作者田辰山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首先非常感谢邀请,让我来参加这样一个重要活动,有一个同在座的中外关心中国道路各方人士的交流机会。我的学术领域是政治学和比较中西哲学。今天就此机会跟各位分享一下,在这样的学术领域,我们是怎样思考新时代中国道路的。
从比较哲学有一个意识,想要看清文化问题,须告别对它抽象、笼统、现象的看待层面;要去它核心内涵深处看;“文化”任何时候都是特定哲学产物,是从围绕的一个特定哲学内核延伸。以往出的问题,是只把投向文化的目光局限在所谓“文化”的项目或现象上。其实还应有很重要的一个视角,是政治学同比较哲学的相结合。
这个相结合领域看问题的方法有两条,一条是中国很多人都知道的“走出庐山”说法:“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说要“走出庐山”,中国要从自己文化出来,走到外边文化里去看一看;然后“知彼知己”——弄懂外边文化是怎么回事,再回过头看自己。这是以懂得外面为基础:也即是说,在当今中国要理解自己文化,必须在了解对方(如西方)文化基础上,才有助于看到自己文化内部看不到,只有从外部才能看到的图景。这是一个比喻,在比较中西哲学领域,我们感觉当今亟需这样一个角度。
第二条是:因为“走出庐山”是走向一个哲学高处新视野。它推荐了个新的思维方法;也是符合辩证法的方法,即变化的、整体的看问题方法。其实这个方法也是优秀中华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体系都强调的、十分有效方法。过去是用它的,只是长期以来不用了,就新了。一句话,要想清楚、说清楚今天这个世界,须转变一个思维模式,要转换一个看问题的角度。
现在缺乏的这个角度,在于“走出庐山”和“走向哲学”的关键是帮助我们有一个离开个人主义角度、走到从关系高度看问题的改变。开始从关系的高角度看问题,不再陷于“单子个体”孤立一己利益的角度;是扩大眼界,从人和社会生生为贵关系为本看问题。
“生生为贵关系为本”是以自然宇宙、天地万物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大生命体系和大生命过程看待。这个有机整体之构成,必然是作为生命载体的,其中一切的不可分联系,都是有利生命生生不已一个“一多不分”体系。“走出庐山”和“走向哲学”,让我们来到一个生态生命哲学,一个贵生、惠生、利生、护生的世界观、社会观和人生观哲学。这个哲学是必然的人与人之间当然互系的、自然的、恰当关系的哲学。它正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一以贯之,至今仍意气风发、突显本色、拥有全人类意义哲学,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用儒家和中华文化传统很熟悉的话说,即是“仁义”;“人/仁”——仁的、人与人当然恰到好处的关系与行为。如果从这样的生态文明哲学与文化思考问题,会忽然发现,我们着眼点必是在于势在必行的、人类要从一个破坏、走向一个有益于人与人“一多不分”恰当关系的哲学文化道路。
对于生态哲学文化,比较中西哲学同政治学二者结合的学术,有两个提法,一个叫做“一多不分”,另一个叫“一多二元”。“一多不分”是天地人大生命体系和大生命生生不息过程,它必然是整体有机、大小任何节点都是生命一体、相系不二与须臾不可分割的组织体系。人在天地间,是同大生命体和大生命过程通彻为一体的,一想就知道,必然是人与人相系不分、同命运共呼吸的。人人都是活在一起的,是一个大家庭,共生共命、相互依存在一起,只能互相帮助而不是什么“相互竞争”。这样生生为贵自然关系组织称作“一多不分”,构成有机生命的生生为贵关系载体。当今人类世界不存在别的选择,必须选择这条生态哲学文化道路。这是唯一一条生路。新时代中国的道路一定是这条生态哲学文化道路,必是致力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从哲学上看到的意义,这是人从同别人“争”到同别人讲“和”的思想意识、价值和行为。
为什么?只是因为“一多不分”是生生为贵关系组织,是贵生、惠生、利生、厚生的功能关系。这是中国文明自古《易经》、《道德经》和儒学经典一以贯之承传至今所讲述的天地宇宙人类社会万物都是一个生命大体系的中国哲学文化,讲的都是这个生命体系和生生不息过程的不可破坏和必须人人通过自己要好好地去抚养和对待。但是“一多二元”恰恰是破坏这个生生不息生态环境,破坏生生不息大生命本身体系和大生命过程关系的。它的要害的、对“一多不分”加以破坏的、有悖于生生为贵关系的哲学谬误性意识,则是把人和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竞争,看成剥夺与征服。
人类理当直面的两个非常明显不同思维走势,很简单,一个是非要斗不可,一个是以力求“和”唯此为大。比较哲学在这个哲学点阐释用的“一多不分”,是一个反映力求“和合”的哲学提法。我们现在住在的“中和”大厦,正是这个“中”、这个“和”,是生命生生不息的必然决定条件;只有“和”,才有生命,才有存活。因此“和”,在比较中西哲学角度审视,是中华文化、文明最根本的核心旨要。要讲中华文明和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必然要讲到这里来。
有了这样一种看问题方法的转变,对于眼前乱云翻滚的、一切人的说辞与行为现象,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我们将都该可以比较容易地好好想:作为今天的人的活动,眼前的所作所为,是贵生、利生、惠生、厚生,是有利于生生不息,还是反其道而行之,还是在破坏这个生生不息?是呵护与培养人和人之间和合的关系,还是相反地千方百计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共命运关系?做出这个辨别判断,是中国对自己信仰、哲学文化、理论、道路和制度有坚定内心认同和充满自信的根基。这是在根基处从比较哲学与哲学视角看问题的自觉认识,是根植在生生不息生态哲学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源自这个根基的中华哲学文化历史传承而产生的现代和当代文明。
这一生态哲学是当今对马克思主义的恰当解释,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是基于生生不息自然宇宙观的哲学。现在已有来自中西的学术研究,说明这个关系。马克思本人思想出现是受黑格尔哲学的理念影响,又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颠倒;而黑格尔理念又同一批西方思想家思想分不开;这一批西方思想家思想又同传教士将中国老子、孔子等等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元素传播到西方有密切的联系。
所以,该是我们在这个意义来看什么是文明。中华文明是以人同人命运共生共存、生生不已关系为中心形成与承传的。中国文明从来不是现代文明那种简单工具理性,不是工具发展的以同别人战斗为目的。应该可以明白了,恰是这里,西方及其他文明开始的它们不了解中华文明,是从这里的不了解中国,才有的对中国扭曲、误读,才把很多负面西方概念,把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套褒贬尺度,强加给中国文化文明事务,统统讲入那本来不属于中国的框架,造成中国文明、文化几乎全部被丑化。比如“民主”、“政党”这等概念,本来是中国传统“一多不分”哲学的“民本”语义;“民主”只能是人民做主;无论谁掌权都必须代表人民,以人民利益为最大利益,否则没有合法性。“民主”词汇今天屡屡给中国意识形态造成混乱、频发乱像和坏事,根子出在把虚构概念“democracy”(迪莫克拉西)同中文“民主”混为一谈。“迪莫克拉西”这个哲学谬误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藤生出的果,是以上帝为缘起,人是由“他”单子个体制成的,才派生“迪莫克拉西”这个概念。
还有,中华文明的“文明”,是“civilization”的汉译;但二者的不同文化语义环境,造成它们根本不可能是同含义的同一词汇。“civilization”是城市化,是类似上帝创造世界含义的形而上学线性历史观,而中文的“文明”不是。“文明”于中国哲学文化是“性即天道观”,是“天人合一”自然宇宙观。我们该认认这个“针”了。其实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中西词汇不对称、语义不相通是个很大的困惑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是用比较哲学和在哲学上看问题,我们今天才得以意识到,竟有这样从哲学根基引发的大规模的深层误读中国。一点不应该怀疑,西方及其他文明开始误读中华文明的地方,将必然是它们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起点,直到最终能意识到中华文明是生生为贵关系为本的文明。也是这里,其实也是我们要责怪自己的地方。中国的文化不自信,是来自不了解始终主导西方的“一多二元”哲学文化。因为对西方哲学文化这种特质不了解,中国才在西方误读中国的地方,也从近代开始误读自己,也随之开始用西方话语误判自己,同自己文化渐行渐远,变得不懂自己。因此同一个原因,当今的中国文化自信,也必然是从这里理解开始。自信从对自己这样的自觉开始。
从现在开始,中国同西方及其他文明一定要互相了解起来,要从中华文明是生态生命哲学构成的文明这里开始。中国曾经不是走出去,不是弄懂了西方才回来看自己,而是一厢情愿、想当然地盲目崇拜;所以今天必须要通过知彼知己,达到对自己别开生面的新理解。很容易懂,这样地转变到一个平白易懂看世界的方法,其根本区别是哲学分歧,是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分歧,是从一种人与人的敌对关系出发的看问题,转到从一种人与人的相互依赖关系出发看问题。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它是一个如此容易、简单的看问题方法的转变。除了心理智障,谁会学不会呢?但是本质的问题是,要不要用一个这样简单的方法来支配我们人人的想法、做法和说法,来矫正和改变人类、世界和中国命运!人人该问问:是真的学不会,还是不想学?的确是需要分析一下,是学会了会给你带来个人失去利益,还是你会意识到根本不该在乎所谓的“个人利益”?
这就是我要介绍的比较哲学和政治学结合的一个简单看问题方法,与大家讨论。谢谢!
【田辰山,政治学硕士、哲学硕士、政治学博士。原北京外国语大学文教专家、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本文为作者最近在一次《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中西对话学术论坛”的发言;徐钧鸿:文字整理。】
「赞同、支持、鼓励!」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cwzg.cn/theory/201911/526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