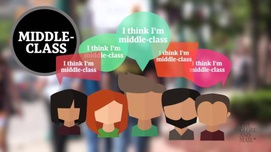平等的悖论——马克思论平等与商品生产的关系
摘要:在马克思看来,不能离开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抽象地谈论平等问题;任何平等观念都是对特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反映和表现;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不同,平等观念也就不同。就资本主义而言,一方面它在商品交换的层面保留了与劳动者个体私有制和简单商品生产相适应的平等观念;另一方面它在商品生产的层面又把这种平等推向了自己的反面,从而形成了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相适应且具有悖论性的平等观念。既不能把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平等观念混为一谈,也不能用简单商品生产的平等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不平等进行辩护。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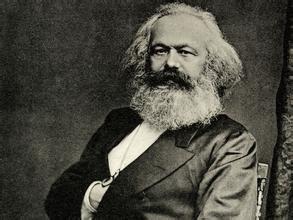
平等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和思想家们不断探索的主题。近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提出了基于所有权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平等观,以此为资本主义的理性王国作辩护。马克思虽然不否认平等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价值,但他认为,不能抽象地理解平等,要把平等植根于现实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之中去理解。为此他把关注的目光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领域转向物质生产领域,进而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揭示出了资产阶级平等观不过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等价交换双方契约自由和意志自由的观念体现,它们服务于且遮蔽着资本统治这一社会实质。从现实生产关系的角度而不是从抽象的价值悬设来寻求人类平等的实现,是马克思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平等观的实质所在。
一、平等的实现与简单商品流通
平等是评价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调解人们之间利益冲突的一种价值规范,这种规范随着历史的变迁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内容和形式。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有朴素的平等观念,但这时的平等仅仅限于公社成员与原始共同体具有天然联系意义上的“身份平等”。到了奴隶社会,平等只是社会的一部分人即自由民所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对于毫无自由可言的奴隶而言是一种“特权”和不平等。而在封建社会,以土地的私人所有和垄断为基础所建立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平等充其量也就是在各个等级内部的平等,而等级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严重的不平等。
近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个人开始从封建的血缘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独立性和自主性不断增强,社会的自由空间不断增大。人们开始由对神圣彼岸世界天国的向往转向对世俗的个人欲望和利益的追求,这促使很多近代思想家开始关注个人权利,在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基础上,基于所有权原则的资产阶级平等观应运而生。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是平等的,因为他们拥有平等的权利,这种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意愿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①。如果说霍布斯把平等归结为自然权利,进而又把自然权利归结为自由,那么,洛克则是把平等的权利和财产联系起来,强调个人财产权的重要性,并把劳动确立为财产权的基础和前提。他明确指出:“我的劳动使它们(指草、草皮、矿石。———引者注)脱离原来所处的共同状态,确定了我对于它们的财产权。”②卢梭基本上延续了洛克的劳动所有权思想和平等观念,认为:“我们不可能撇开劳动去设想新生的私有观念。我们不可能理解一个人要把原非自己创造的东西据为己有,除了因为添加了自己的劳动以外,还能添加什么别的东西?”③这些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都坚信,在以劳动所有原则为基石的资产阶级王国中,“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④。
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统治地位的财富形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做的“人体解剖”,正是从商品生产和交换开始的。也正是在对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分析中,启蒙思想家的劳动所有原则和以此为基础的自由平等观念开始进入马克思的视野。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经济的到来,首次实现了现代意义上人和人之间的平等。
首先,从主体方面来看,“作为交换的主体,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在他们之间看不出任何差别,更看不出对立,甚至连丝毫的差异也没有”。因为,“每一个主体都是交换者”,也是商品的所有者,他们具有同样的规定,或者说“他们处在同一规定中”。⑤
其次,从对象方面看,“他们所交换的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是等价物,或者至少当作等价物”。作为等价物,“它们不仅相等,而且确实必须相等,还要被承认为相等”。⑥这就是说,要想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就必须出让自己的商品,而且是价值相等的商品。在等价交换的意义上,各个主体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等价交换是每个商品交换者作为平等的人的现实基础。当然,这是一种总的趋势和结果,是在本质和规律层面上的把握。就交换的个别存在而言,等价交换偶然性居于统治地位,不等价交换的存在是一种常态和普遍现象。对此,马克思指出,在交换中,“如果一个人欺骗了另一个人,那么这种情况不是由于他们借以互相对立的社会职能的性质造成的,因为这种社会职能是一样的;他们在社会职能上是平等的;而只是由于有的人生来狡猾、能言善辩等等造成的,总之,只是由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具有纯粹个人的优势造成的。”⑦并且等价交换以及在此基础上确立的商品交换者的平等关系这一本质和规律,恰恰是在无数偶然和不平等的交换中实现的。在谈到简单商品流通公式时,马克思说:“诚然,在W—G—W中,两极W和W,如谷物和衣服,也可能是大小不等的价值量。农民卖谷物的价钱可能高于谷物的价值,或者他买衣服的价钱可能低于衣服的价值。他也可能受衣商的骗。但是这种价值上的差异,对这种流通形式本身来说完全是偶然的。……在这里,两极的价值相等倒可以说是这种流通形式正常进行的条件。”⑧
再次,从人们的需要和对需要的满足来看,“只有当个人B用商品b为个人A的需要服务,并且只是由于这一原因,个人A才用商品a为个人B的需要服务。反过来也一样。每个人为另一个人服务,目的是为自己服务;每一个人都把另一个人当作自己的手段互相利用” ⑨。这就是说,各个主体之间是一种互为手段和工具的关系,在此意义上,他们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最后,从货币等价物来看,在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面前,不仅商品交换者,而且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例如:“对卖者来说,一个用3先令购买商品的工人和一个用3先令购买商品的国王,两者职能相同,地位平等———都表现为3先令的形式。他们之间的一切差别都消失了。卖者作为卖者只表现为一个价格3先令的商品的所有者,所以双方完全平等,只是这3先令一次是以银的形式存在,另一次是以砂糖等等的形式存在。”⑩马克思从货币商品的本质层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及其现实基础所做的阐释,极为深刻而独到。这涉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思维抽象方法,这种抽象至少包含了三个不同的逻辑层级。⑪第一个层级是从使用价值中抽象出价值。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商品都表现出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方面。使用价值指的是商品靠自己的属性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不同的商品,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也不同。因此,在使用价值的层面,一种商品无法和另一种商品比较优劣。在商品交换条件下,一种使用价值和另一种使用价值之所以能相互交换,就是因为他们背后的“统一物”,即“人的生命力消耗的结果,是对象化劳动”。 ⑫凝结在不同使用价值上的人类劳动形成了商品的价值。劳动只有量的差别,而没有质的差异。
第二个层级是把“个别劳动时间”抽象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认为,在商品社会里,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个人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为每一个人的劳动,只有通过和他人劳动的交换,进而实现从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换,进而进入社会的劳动系统,从而获得社会性,其劳动时间才能从个别劳动时间转化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获得社会的承认。因此,“在交换价值中,个人的劳动时间直接表现为一般劳动时间,而个别劳动的这种一般性直接表现为个别劳动的社会性。”⑬
第三个层级是把货币抽象为价值存在的“独立形式” ⑭。马克思认为,货币不过是在商品交换中分离出来的特殊商品,是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是“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 ⑮。通过货币这样一个一般等价物,人作为货币的所有者不再被分为三六九等,而是变成了没有任何差别的存在物。“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⑯通过这三个层级不同的抽象,马克思不仅揭示了平等在商品交换条件下的独特含义,而且剖析了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即根源在于商品生产中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这种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使得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消失,从而实现人的平等。在W—G—W的简单商品流通中,不同的商品在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以货币为媒介相互交换,不仅使平等关系得以实现,而且使平等的观念在人们的意识中产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这种基础而已。”⑰
可见,商品生产打破了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存在的隶属和依附的种种不平等关系,首次在“经济的”意义上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并且,“除了平等的规定以外,还要加上自由的规定”。因为,“尽管个人A需要个人B的商品,但他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这个商品,反过来也一样,相反地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商品中去的人格。因此,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人格这一法的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由的因素。谁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每个人都是自愿地转让财产”。⑱因此,马克思并不否认在商品交换中存在的普遍的平等和自由关系。但是,这只是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情景,启蒙学者的所谓的劳动所有原则,只适合于劳动者的个体私有的简单商品生产的原则。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自由平等原则却走向了反面。
二、资本流通与向不平等的转化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不同于简单商品生产的另一种经济形态。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只存在于个别的、特殊的领域,还没有成为一般的、普遍的关系。历史上,资本主义社会首次实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的一般化和普遍化,不仅一切劳动产品都成为商品,而且劳动力自身也转化为商品。作为自由劳动者,工人既不像奴隶、农奴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也不像自耕农那样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相反,他们脱离了生产资料而获得了自由,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实现了分离。马克思写道:“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⑲
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自由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虽然和简单商品生产中的等价物交换相类似,但又本质上不同于简单商品生产中的商品交换关系。
首先,在交换中工人与资本家的身份和地位是平等的。一方是作为劳动力占有者的工人,另一方是作为货币占有者的资本家,他们“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 ⑳。或者说,“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 21。
但是,“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22。就是说,只要进入生产过程,工人与资本家的身份和地位就不再平等,工人并不是“工人”,而是劳动力商品的占有者;资本家也不是“资本家”,而是货币的占有者。而当工人作为“工人”、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发生关系的时候,这种关系决不属于简单商品生产,而是属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并且,他们之间绝不是平等的。这种“两面性”被杰拉斯称为“工资关系的互补方面”,即“在流通领域,是自由缔结的平等的交换契约;而在生产领域,则是无酬的数小时强迫劳动”。23
因此,尽管说“流通本身不会产生不平等,而只会产生平等”24。但是,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的工人来说,“这种平等已经被破坏了,因为这种表面上的简单交换是以如下事实为前提的:他是作为工人同资本家发生关系,是作为处在与交换价值不同的独特形式中的使用价值,是同作为价值而设定的价值相对立;也就是说,他已经处在某种另外的在经济上具有不同规定的关系中了”25。资本家手中的货币商品与工人的劳动力商品,具有经济上不同于简单商品生产的规定,或者说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关系。
其次,在交换中,工人和资本家是一种等价平等的交换关系。“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其中,所谓的“平等”,即一方是作为劳动力的卖者的工人,另一方是作为劳动力的买者的资本家,“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26人让渡自己的劳动力商品,资本家则支付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因此,对工人来说,“他在这个交换中就是作为平等者与资本家相对立,像任何其他交换者一样;至少从外表上看是如此”27。依据此文,在“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中,罗伯特·塔克和艾伦·伍德等人断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并非不正义。如伍德认为:“用工资来交换劳动力,这是发生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唯一交换。这是正义的交换。”28
但是,一旦把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联系起来,就会看到,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交换并非是等价交换,“劳动者没有得到与他所创造的剩余劳动相对应的等价物”29,因而并非是平等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在工资交易中劳动力的买卖是如下事实的‘自然结果’,即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但是没有劳动力,而工人则是拥有劳动力但没有生产资料”30,这就决定了工人的劳动过程不再像简单商品生产那样是为了生产出某种使用价值,而是资本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为中介实现自我增殖的过程。因此,流通领域的自由和平等只是“骗人的表面现象”,它掩盖着资本主义实际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31这里所说的“这一过程的背后”,就是指“生产领域”,而这个领域恰恰是很多资产阶级思想家在阐释平等和自由时所忽视的地方,也是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秘密所在。
第一,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要大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劳动力商品不同于其他商品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32。工人不仅在必要劳动时间内生产出和劳动力价值相当的价值,而且还在剩余劳动时间内生产出剩余价值。所以,表面上看,资本家支付的工资是工人全部劳动的报酬,实则只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工资只能补偿工人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耗费的必要劳动,而剩余劳动,则被资本家无偿地据为己有,并没有支付任何等价物。
第二,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是“活劳动”,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则是“死劳动”。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工人已经不能以其他商品的形式,以对象化劳动的形式换出自己的劳动,他能够提供的可供出售的唯一商品,就是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活劳动能力”。33这个活劳动能够不断地为资本家创造出价值,实现抽象财富的增长。所以马克思说,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中,“买来的使用价值直接就是提供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即创造价值的使用价值”34。而资本(包括以工资形式存在的不变资本)不过是一种“死劳动”,它必须依靠活劳动才能实现增殖。“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35资本因工人的劳动而获得新生,工人的生命则因劳动的耗费而不断衰竭。
第三,工人的劳动是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而资本家的管理、监督等所谓的劳动则是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因为,当一个人的劳动是参与价值创造的“管理劳动”时,他就决不是剥削劳动的资本家而是一般劳动者;而当他是资本家的时候,其劳动就决不是创造价值的“管理劳动”而是一种“剥削劳动”。36对此,马克思说道:“如果资本家的劳动被看作是在工人的劳动以外并且同工人的劳动并列的特殊劳动,如监督劳动等等,那么他也会像工人一样得到一定的工资,于是他也就属于工人的范畴,而决不是作为资本家同劳动发生关系了。”37
马克思用“所有权规律”向“无偿占有规律”的转化,揭示了在平等交换假象下存在的不平等交换,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特有的现象和规律。他说: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至少我们应当承认这样的假定,因为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但是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38这后一方面,既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对启蒙思想家的劳动所有原则实践的超越,也是马克思对启蒙思想家基于劳动所有原则的自由和平等观理论的超越。
再次,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在于追求价值增殖,“资本主义财产权并不仅仅是一种个别生产者的个别财产权制度,而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种财产权制度”39。在这种财产权制度下,工人沦为纯粹的手段和工具,打破了存在于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中劳动者互为目的、互为手段的平等关系。此外,资本流通和简单商品流通也有着本质的不同。在W—G—W这一简单商品流通中,“始极是一种商品,终极是另一种商品,后者退出流通,转入消费。因此,这一循环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是满足需要,总之,是使用价值”。而在G—W—G这一资本流通公式中,始极是货币,终极也是货币。因此,“这一循环的动机和决定性目的是交换价值本身”。40“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而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41资本的运动没有限度,资本的剥削没有限度,工人只是实现资本的运动和剥削的一个对象条件和中介物。
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社会出现了“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并行不悖的奇特现象,社会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这种不平等现象有不断加剧的趋势。一方面,生产劳动者一无所有,与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致富相背离,出现了具有“悖论性”的劳动者越劳动就越贫困的现象,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不是把它本身的现实性变成自为的存在,而是把它变成单纯为他的存在,因而也是变成单纯的他在,或同自身相对立的他物的存在。”42 另一方面,非生产劳动者不参加劳动却拥有了一切,劳动与劳动相对立的客观财富世界的对立越来越扩大。“财产同劳动之间,活劳动能力同它的实现条件之间,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之间,价值同创造价值的活动之间的这种绝对的分离”43,“劳动本身越是客体化,作为他人的世界,———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同劳动相对立的客观的价值世界就越是增大”44。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劳动所有原则,现在变成了“劳动”和“所有”的分离,变成了对他人劳动的无偿占有;基于劳动所有原则的自由、平等理想,现在则变成了压迫、剥削和专制的残酷现实。这样,“所有权在资本方面就辩证地转化为对他人的产品所拥有的权利,或者说转化为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转化为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而在劳动能力方面则辩证地转化为必须把它本身的劳动或它本身的产品看作他人财产的义务”45。
可见,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生产者对自己的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所有权对资本家来说表现为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象征平等和自由的“等价物的交换”是存在的,“不过,它仅仅是这样一种生产的表层而已,这种生产建立在不通过交换却又在交换的假象下占有他人劳动的基础上”。46资本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商品生产条件下,只要“存在着使剥削成为不正义的更深的不正义———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47,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和自由的实现。一如马克思所说的:“表示交换价值相交换的简单规定中的平等和自由”与“资本的规定性”上的平等与自由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在后者,“这种平等和自由证明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48这种悖论表现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内在特质。因为,“资本本身就是矛盾”49,“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50。
三、方法论启示与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分析表明,任何平等观念和价值判断都是对特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反映和表现;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不同,平等观念和价值判断也就不同。前者构成后者的实际内容,后者则是前者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平等观念和价值判断。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讲道:“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51作为一种“权利”,资本所要求的平等,就是剥削劳动的平等,就是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的平等。从资本方面看,这种平等权利可以体现为:“资本家自己叫喊着要求平等的竞争条件,即要求对劳动的剥削实行平等的限制。”52例如:在使用童工的问题上,“因为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说,它要求把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的平等当作自己的天赋人权,所以,儿童劳动在一个工业部门受到法律限制,就成为儿童劳动在另一个工业部门受到限制的原因”53。对于广大工人来说,资本主义的平等权利就意味着,“一大群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各种各样的工人,争先恐后地向我们拥来,简直比被杀者的鬼魂向奥德赛拥去还要厉害。即使不去参看他们腋下夹着的蓝皮书,我们也可以一眼看出他们劳动过度。现在让我们从这一大群人当中再挑出两种人来,一种是女时装工,一种是铁匠。这两种人的鲜明的对照表明,在资本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54。资本无差别地剥削工人,反之,工人无差别地接受资本的剥削从而劳动过度,这就是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平等要求。因此,不平等交换,即资本家无偿地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亦即剥削,在个体劳动者看来,它是不平等的;而在资本家看来,它却是平等的。或者说,如果立足于个体私有制和简单商品生产,它就是不平等的;如果立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它就是平等的。
把平等观念和价值判断与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联系起来,把劳动者个体私有制和简单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平等观念,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平等观念区分开来,既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内容和核心原理,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的鲜明体现。按照《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表述,这种方法“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55。因此,不与特定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平等是抽象的,而任何抽象的平等都不过是“意识形态家”的一种虚构。当然,《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的马克思,由于经济学知识的缺乏,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内部对资产阶级的平等观进行深入的剖析。但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应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解剖,深刻地揭示了平等和商品生产的复杂关系。一方面,简单商品生产构成了现代平等观念最深厚的土壤,体现了商品交换中拥有不同商品的主体之间地位平等和契约自由;另一方面,扎根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现代平等观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开始向其反面转化,形成了交换过程或流通领域的平等和生产过程或生产领域的不平等,亦即形式平等实则不平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深邃之处就在于,他把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引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透过交换过程或流通领域的平等看到了生产过程或生产领域的不平等,实现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批判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批判的有机统一。
遗憾的是,无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都离开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抽象地谈论平等问题或提出各种平等要求。空想社会主义者在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的不自由、不平等和不正义现象时,对劳动者充满同情和愤怒,并以正义和平等为标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剥削和奴役现象进行了强烈的道德批判和谴责。对此,恩格斯指出: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56道理很明显,既然说任何平等观念都是特定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的表现,那么,如果不诉诸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任何平等要求都将沦为一种苍白无力的道德义愤和说教。
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也同样如此,他们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混同为劳动者的个体私有制,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混同为简单商品生产,有意无意地用简单商品生产层面的自由和平等来掩盖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对此,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它忘记了,后者不仅与前者直接对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57“经济学家们为要证实资本的合理,替资本辩护,就求助于这个简单的过程,恰好用这个使资本不能存在的过程来说明资本。为了证明资本,他们就证明资本不存在。”58“和谐经济论”的倡导者巴师夏就是这样,他“企图证明,经济关系到处都表示同一些简单规定,因而到处都表示交换价值相交换的简单规定中的平等和自由。这完全是儿戏般的抽象法”59。把小私有制和简单流通的土壤里孕育和确立起来的自由和平等,看成是大私有制和资本流通所具有的自由和平等,并为后者的合理性进行辩护,这在逻辑上就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面对未来,马克思不是虚构一个彼岸世界的平等理想,而是在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实际变革中,寻求对资本主义平等观念的超越和对新社会平等理想的实现。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从来不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建立在这样的(指平等的道德要求。———引者注)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我们眼见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溃上。”60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存在着形式平等和实质不平等的矛盾,具有虚伪性和历史局限性的资本主义平等最终必然会被扬弃和超越。而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就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之中。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就必然存在着剥削、不平等和非正义。只有推翻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实现社会生产“目的”的革命性转变,即从为资本增值服务向为人的发展服务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物的增值与人的贬值和形式平等与实质不平等之间存在的矛盾。这是马克思超越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超越一切自由主义者的实质所在。对于马克思的平等观,恩格斯的这段话无疑是最好的注解:“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61马克思的这一平等观,对于我们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平等观的精神实质,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童萍:北京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副教授,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6第6期,作者授权察网转发。)
①[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97页。
② [英]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9页。
③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2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95—19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95—196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95—196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176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98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01页。
⑪ 有学者提出马克思经历了两次抽象化。参见王代月:《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马克思经济政治学》,载《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421页。
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424页。
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326页。
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06页。
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155页。
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99页。
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98页。
⑲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677页。
⑳ 同上书,第195页。
21 同上书,第204页。
22 同上书,第205页。
23 [英]杰拉斯:《关于马克思和正义的争论》,姜海波译,载李惠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6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01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43页。
26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04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43页。
28 [美]伍德:《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林进平译,载李惠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第20页。
29 [美]胡萨米:《马克思论分配正义》,林进平译,载李惠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第60页。
30 [加拿大]艾伦:《马克思恩格斯论资本主义的分配正义》,王贵贤译,载李惠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第109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02页。
32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26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398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399页。
35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69页。
36 王峰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当代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上)第278页。
38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673—674页。
39 [加拿大]尼尔森:《马克思论正义:对塔克—伍德命题的重新审视》,林进平等译,载李惠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第207页。
40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75页。
41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78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45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43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47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50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505页。
47 [加拿大]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33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04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542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05页。
51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38页。
52 同上书,第564页。
53 同上书,第457页。
54 同上书,第294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4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56页。
57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76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82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04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1卷第209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13页。
「赞同、支持、鼓励!」
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维护费用及作者稿费。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如考虑对我们进行捐赠,请点击这里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cwzg.cn/theory/201702/345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