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要去延安——延安时期知识青年的“朝圣”之旅
延安时期,知识青年喊着“我要去延安”的口号奔赴革命圣地,经过革命熔炉育英才,他们茁壮成长起来,然后深入到各条战线,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正如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说:“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现在传下来了,以后更要继续传下去。”知识青年树立起一座爱国奋斗的永恒丰碑,至今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当代青年学习。

孙锡良:“院士”在向“爵士”进化?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显然是必要的。但是,应该是真心尊重知识和人才,应该是尊重真的科技人才,而不应该是尊重权力型人才,不应该是尊重财富型人才,绝不应该尊重学棍型人才。真的科学家,真的科技精英,国家给予多高的待遇,老百姓都会鼓掌通过。科学的殿堂一旦沦为权力和财富的角斗场,“院士”迟早都会变成“爵士”,老百姓迟早会放弃对院士们的崇敬。院士爵士化是对科学与技术的最大不尊重。

少年,你想要哪种超能力?
平民想要获得知识、力量,也不是不可以,北大的图书管理员,曾经创办过工人夜校,创办过农民讲习所,免费教给大家知识,免费告诉大家——团结就是力量。知识就是力量,但这力量,需要大家解放自己,通过团结互助去获得。劳动阶层没有什么超级英雄,也不该指望什么超级英雄,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想要创造美好生活,只能靠我们自己!

“铁人”为何会痛哭?
“工匠精神”不是一朝一夕丢失的,也不是现在的工匠阶层想拥有就能拥有的。只要反问一句便可了然:当下我们缺少的仅仅是“工匠精神”吗?我们社会的许多领域、阶层,已然丢失了应有的“专业精神”:为什么如今少有让人吃着放心的农产品了?“舌尖上的食客”们,常常是在无奈的情况下进食;知识界本应探求真理,严守学术规范,而频繁的“论文造假”又如何解释;官员本应以身作则,为人民服务,却屡屡有贪腐堕落之徒落马……

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劳动人民的现实
西方所恶意散布的诸多歪理邪说之所以能够在知识分子中大行其道且畅通无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从应试教育中脱颖而出的中国知识分子过于依赖书本知识来认识和了解社会。社会主义制度所提供的生存保障,本意是为了解除知识分子的后顾之忧,以便他们能够全力以赴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之中。但是,在免遭衣食之忧以后,他们也就脱离了活生生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以及广大劳动人民所生存的社会现实,变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养尊处优的书呆子。理想一旦脱离现实,就变成了荒唐可笑的空想。

张文木丨战略学札记·人生之二:生死之地有真理
青年喜欢从事物内部读康德思想,认识到“二律背反”是世界存在样式,知道彼岸世界是可以批判的,但这时期的批判往往是无限的,因而是幼稚的。老来知道从事物外部理解康德的世界,知道事物的存在是有限的,有限性产生于事物的相互规定之中,自我约束才是人的力量源泉。消灭有限性——不管这是个人还是国家行为——的同时也消灭了自己。完成了从批判别人到批判自己的循环后,人生也就进入不惑和天命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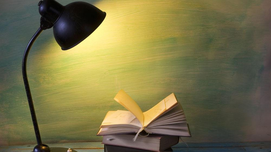
知识是如何被资本私有化的?
知识是几代人或社会群体共同劳动的结果,具有公共品性质。知识的私有化是历史性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为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通过雇佣劳动、知识产权、全球分工等方式无偿占有公共的、他人的知识。知识的资本占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知识的积累和财富的生产,但资本积累的内在需求规定了知识进步的方向,限制了知识积累的持续性和创新能力的提高。重新审视知识私有化的历史性和局限性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问题。

知识改变命运?在美国也是个“故事”
和二三十年前我们年轻的时候相比,我们在高等教育中面对的债务风险大大增加了。在盈利性学院中,这一问题尤其严重,因为其学生更可能来自贫困家庭,或者在贫困线附近徘徊的低收入家庭。正因为如此,盈利性学院的目的,根本就不能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改变他们的命运。


知识精英“去中国化”导致博学的无知
当前知识界有种现象,那就是但凡有专业的人都试图将自己的学科知识作为议论和评判政治的标准。但问题是,很多人关于政治、尤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判断都是一错再错,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关于政治的知识实在太少。正因如此,笔者认为知识精英们在谈论政治时应该保持审慎和低调。

构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刻不容缓
当今中国,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是构建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一方面,这是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当代中国也为这个任务的完成提供了极好的社会条件。中国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顺应时代需要,以建设性的态度,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大胆创新,创造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思想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