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专栏
-
 察古知今
察古知今胡新民:程潜父女眼中的毛泽东
前几年程熙回忆起毛主席,评价说:“我觉得毛主席这个人对下层、对老百姓有一种爱,拿现在来说,我们现在就是缺乏对普遍的爱,因为有爱才有一个志向,要为大多数人再谋福利。在我印象中,我觉得毛主席是一个很伟大很平易近人的人,很有人情味,也是个诗人。他不像我们讲的一些官员,好像有架子,你看到他很害怕。(和他在一起)很随便,你可以随便发表你的意见。他可以给你这么一个感觉,你在他身边的时候,不觉得他是在天安门挥着帽子的那个伟人,而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老人,就是一个普通人。”
-
 察古知今
察古知今胡新民: “两弹一星”元勋——优秀共产党员群体
钱三强这位1954年入党的“两弹一星”功臣,在1955年1月15日的那次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上课时,深深感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魅力。他回忆,当毛泽东和他谈到原子核内部组成情况时,他立刻感到“这是一个预言,是一位政治家的哲学预言。”当毛泽东拍板“现在到时候了”时,他立刻联想到美国的罗斯福经过科学家再三提醒决定搞原子弹的往事,“是不是凡属政治家都很快地对重大科学问题有远见,能及早把目光投向未来呢?”“我们中国的原子核科学家,在这方面应该说一直是幸运的。国家最高层不但有果断的决策,实行决策的条件、措施也都在周总理的运筹之中。”“就这样,许多办不到的事情办成了,难以出现的奇迹出现了。”
-
 察古知今
察古知今邓小平为何如此重视对《苦恋》的批评
1984年2月28日,邓小平在和薄一波的谈话时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长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也将会是长期的,因此反对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将是长期的。3月14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在谈到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时指出:过去一段时间,精神污染搞得很厉害。我说过,那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二中全会后,整一下精神污染,很有必要,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风刹住了。起码现在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再搞二中全会以前那一套了。同精神污染的斗争,是长期斗争,要做长期的工作。
-
 察古知今
察古知今毛泽东是如何与西方大国打交道的
富尔回国后,根据毛泽东向他分析的中国法国和美国之间的利害关系,出版了主张改善中法关系的《蛇山与龟山》一书。书名体现了富尔的匠心:来自毛泽东的一句诗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当时在野的戴高乐看过这本书后,写了一封长信称,他完全赞同书中的观点。1958年年末,戴高乐当选总统。68岁的他开始正式考虑缓和与东方、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5年后,戴高乐仍然对《蛇山与龟山》一书记忆犹新。
-
 察古知今
察古知今让英美议会制度在中国彻底没戏——整风反右的影响
仍然值得警惕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一切机会不遗余力地大肆攻击党的基本路线。有的宣扬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是“普世价值”,鼓吹中国只有全盘西化才有前途,鼓吹“宪政民主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有的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妄图搞乱人心,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此,我们的态度是,对一切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坚决扞卫党的基本路线,扞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察古知今
察古知今作家笔端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
《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卷还认为,最能体现这个时代精神风貌的时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前半期,《党史》二卷是这样描述的:“帝国主义越是封锁,国民经济越是困难,人民却越是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是因为,人民群众坚信,党所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代,一个乐于奉献的年代,一个理想闪光的年代和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这种时代性的社会风尚和思想氛围,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
 察古知今
察古知今胡新民:《蒋介石日记》究竟有多少可以相信?
通过西安事变关于蒋介石日记的上述史料,不难看出,蒋无论是在写日记方面,即怎么写,写什么,包括后来应该怎么修改,还是在用日记方面,即什么时候展示出来,展示什么内容,以期达到什么目的,等等,都是煞费苦心的。因此,汪荣祖认为蒋介石的“日记里有很多言不由衷的话,梦想的话,一厢情愿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也正因为如此,蒋“日记抗日”才留下了那些自相矛盾的情节和难以自圆其说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日记》作为历史资料的价值确实还是有限的。
-
 察古知今
察古知今胡新民:毛泽东没有说过“死3亿人没关系”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有多处涉及到中国应对核讹诈这个话题,现在来看看与“3亿人”有关的两次。第一次是网上提到的“即席演说”,即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这个发言中根本没有什么“死3亿人不算什么”之类的话,也没有“具体谈到中国时”中国会死多少人之类的内容。毛泽东只是针对有人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预言,说出了“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还特地重申了中国的“希望和平”。把毛泽东的这种对全世界人口“极而言之”的估计和中国“希望和平”的意愿解读为“死3亿人不算什么”,显然是一种有意无意的误传和误读。
-
 察古知今
察古知今淞沪会战再思考:蒋介石从未放弃与日本媾和的想法
蒋介石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同意日本的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中国会发生革命。”“假如同意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国政府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由此可见,“中国人民之情绪已达沸点,不能抗日之政府,决不能继续当政。”作为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政府,最好的选择只能是坚持抗战。不过,此后蒋介石并没有放弃过与日本媾和的想法,甚至在英、美、苏先后卷入二战,并逐步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以后。“在1943年10月的同一周里,重庆政府并非只在‘靠不住的盟友’一边下赌注,也与南京汪伪政权保持联系”。
-
 察古知今
察古知今国家公祭南京大屠杀的意义:铭记伸张正义之艰难
除了日本人的错误认识外,西方国家对南京大屠杀相当漠视。这也是为南京大屠杀完全伸张正义的一个重要障碍。二战以后,以西方为主的国际舆论对待德、日的侵略历史的态度迥然不同。假如德国出现对反犹“大屠杀”的罪行质疑的说法或者德国教科书里出现为德国侵略辩护的内容,那肯定是完全没有市场的。对比之下,日本社会一再发出为日本侵华辩护的奇谈怪论,经常公然举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活动,而抗议的往往只有中国人和海外华人。二战时的反法西斯盟友们竟然鲜有反应,那些十分关心中国的西方媒体对此类事也鲜有问津。
-
 察古知今
察古知今宪法学泰斗许崇德眼中的新中国宪法历史
“五四宪法”颁布之后的“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因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都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新形势相差太大。按照常规,“八二宪法”是应在“七八宪法”基础上进行修改,但实际情况已经不允许了。1980年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后,修宪实际负责人彭真于1981年7月专门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认为“七八宪法”过于简单,不如以“五四宪法”为基础进行修改。这个意见被中央采纳。这样,共和国宪法面临的就是一场“大修”。
-
 察古知今
察古知今黄万里反对建设三门峡工程吗?
正如毛泽东1966年4月10日在一份关于建设三峡工程的批示:“需要一个反面报告”一样,像黄万里这样的反对者,在民主决策过程中是很有积极作用的。一些反对意见可以使论证更科学,实施过程更完善。在这个角度上,他们的贡献应该肯定。无论是三门峡工程,还是三峡工程,黄万里敢于直抒己见的精神都应该肯定。但是,如果不顾历史事实去神化他,那完全是错误的;如果还借此来否定中国在建设项目上的民主决策过程,甚至上纲上线,那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实在是有些糊涂了。
-
 察古知今
察古知今从邓小平讲话理解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长期存在
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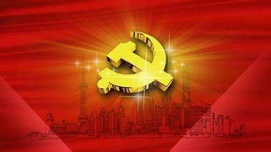 察言观行
察言观行驳许教授:“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文革用语吗?
十九大的召开,宪法和党章都进行了重要的修改。笔者认为,这也为“宪政”专家学者和某些党内的高级干部,特别是尚健在的某些离休老干部送去了一副“清醒剂”。修改后的宪法,除了序言部分的四项基本原则外继续保留外,在正文部分第一条增加第二款:“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样,某些《××春秋》老人终于明白,\"从宪法的第1条到第130多条,没有‘共产党领导’这五个字,从头到尾找不到”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
 观风察俗
观风察俗从习仲勋与吴祖光夫妇的交往看时代的变与不变
吴欢认为习仲勋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竭尽所能团结党的朋友,因此也在大批文化界人士心目中建立起了崇高的威望。习仲勋知道象吴祖光这样的知识分子“自恃和共产党渊源深厚,想说什么说什么,谁都不怕”。但习仲勋更知道“吴祖光是个好人,对这样的人我们党一定要团结。如果像吴祖光这样的人都不能团结的话,我们党将会失去很多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