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有余奉不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统一累进税小记
党的政策使占边区人口最大的贫雇农生活出现了明显的改变。农民手里有了土地勇于向土地投资,增加了粮食产量,改善了生活。阜平是河北着名的贫穷地方,往年一到春初,人民便饥饿无粮,眼巴巴等待着树叶充饥。老百姓把杨树叶叫“杨大人放账”,抗战前为争杨树叶而打架的事也是常见现象。往年,人民赶集总是带着糖菜饼子,而到了四五年抗战结束前带的是黄米干粮,以前每人每年穿不到一小匹布,到1944年是平均每年两小匹布还多了。美军观察组陆登少校,曾在阜平城厢集上看见农民拿着一大把、一大把的钞票,买很多东西回家,他惊叹不止,赶紧拍照留念。也正因为中共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才能动员绝大多数的农民进行抗战,也就赢得了中国的未来。

智广俊:民科出身的育种家何以获奖
袁隆平、李登海、裘志新所以能搞出突破性育种成果,首先得益于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科技工作方针好,社会环境好,科学技术界学风好,使他们能够脱颖而出。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的拼搏奋斗,创造性的科研工作。进入新时期,党和政府为他们育种研究提供了更为优越工作条件,我记得新闻报道过,当年李鹏总理就动用了总理特别资金,来资助袁隆平的育种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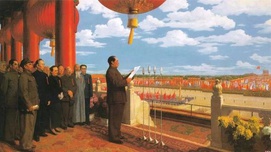
开国大典上,一位翻身农民的致敬
依靠人民,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1949年1月结束的淮海战役,人民解放军正规军60万人,而支前民工达到了200万多人。他们推着独轮车,运送粮食,运送弹药、运送伤员....这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任是什么样主义的感召,宣传的魔法,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动员起这样庞大的力量,这只能发自于民众的真心志愿,他们愿意为自己的子弟兵倾其人力物力。

吕新雨: 农村集体经济的道路与制度
没有社会建设的经济行为一定会失败。单纯的经济性扶贫难以形成持久的造血功能,关键就在于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没有形成有机的联系。没有有效的社会建设,后果只能是贫富的两极分化。塘约村、蒲韩社区和郝堂村的三个案例,呈现出当代中国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路径的多样性,也说明了只有在维护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才能有真正经济的发展,才能克服和战胜资本主义市场对社会、社区的破坏。

阿蒙 | 运筹土改顺民心,决胜战场除“蒋祸”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有的农民分到了土地后,每天都要到地里看几遍。有的农民跑到刚分到的地里,跪下来抓起一把土放在心窝上,抬头望着天空半晌说不出话来,两行热泪顺着眼角往下流。招远县一位老农手捧着新发的土地证老泪纵横,他说:“地契呀地契,我想你一辈子了,你在地主手里打一斗,到我手里得打两斗,要不我死给你看。”解决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就激发了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的勇气,解放区的农民踊跃参军、支前。从1945年9月到1949年10月,山东解放区掀起4次大的参军热潮,有95万青壮年(包括冀鲁豫解放区山东部分参军人数30万)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期间,仅淮海战役山东就出动225万民工支前,向前方运送粮食、弹药,向后方转运伤员。

周恩来是怎样做老区扶贫工作的
周恩来重视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员干部终身学习的榜样。新时期的扶贫工作,就需要扶贫干部扑下身子、放下架子、迈开步子、走出院子,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多搞调查研究,综合钻研贫困地区扶贫难点,寻找脱贫致富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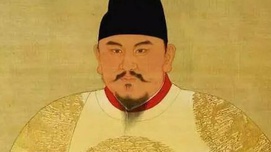
李晓鹏:朱元璋的“阶级意识”
朱元璋虽然当了皇帝,但他还是站在贫苦农民的立场来想问题,他所能了解到的日常生活,就是底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帝国制度下,要当好一个官员必须面对哪些具体而复杂的问题,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没有当过官,不晓得当官也有当官的难处。他所能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官员压迫老百姓的世界,那些官老爷们都很威风、也很腐败。所以,要求他们过一过跟农民差不多的生活,杀一杀他们的威风,在朱元璋看来就是完全应该的。也就是说,不管在阶级感情还是阶级认识上,朱元璋都是从农民阶级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李鸿章,他值得某些人去拼命洗白吗?
一些人只看到了李鸿章的艰难不易,却没看到他的私心自保没有担当;一些人津津乐道于李鸿章搞洋务办了多少实业、建了多少兵工厂,却没看到李合肥拿着朝廷的海量银子,将实业办得多么糟糕,并在其中大肆中饱私囊;当李鸿章用“我只是一个裱糊匠”自嘲,引发许多人“理解”与同情的时候,他们想不到的是李鸿章在那种环境下,也只愿去做一个裱糊匠,而不愿做以身许国不计安危的商鞅。李鸿章爱国吗?从某个角度来说,他是爱国的——毕竟大清给了他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一等肃毅伯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头衔与位高权重的官职,基本实现了当年“一万年来谁着史,三千里外觅封侯”的夙愿。说他不爱大清,肯定不合常理。但是,他爱的是那个能给他高官厚禄的朝廷,而不是大清国的江山社稷,更不是大清国的亿万子民,李中堂只是一个狭隘的“爱国者”;同时他的“爱国”有一个前提,不能损伤自己的利益。当个人权利与爱国发生冲突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先保全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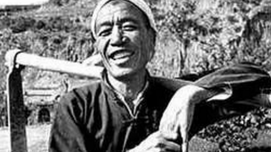
陈永贵如何带领大寨村弱劳力生产致富
第一年秋天,“老少组”平均亩产高达150斤,而“好汉组”则只有120斤。到1949年,“老少组”又创出了平均亩产169斤的新纪录。于是,一些农户退出了“好汉组”,加入了“老少组”。到1948年,“老少组”扩展到29户。到1949年冬天,“老少组”扩展到了49户,占了全村户数的70%。同时,“老少组”也从忙时互助的临时互助组发展成为长年互助组。后来,陈永贵被选为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大寨村民改土造田,抵御自然灾害,把穷山恶水的穷山沟建成了稳产高产的良田,成为中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迄今,在全国各地,许多在“学大寨”过程中修建的水利工程,仍然在发挥着作用。

大寨科学发展:从科学造田到科学种田
大寨是集体经济,有了一个稳定的集体文化,就是合作文化,而不是单干文化,大寨人最讲究自力更生,最善于独立自主。这些在市场经济里,也是具有先进性的,无疑也是具有超前性的,所以,当1990年代以后,郭凤莲回到大寨,大寨依然走在共同富裕之路的前列。大寨合作文化,为什么具有如此强的生命力,这是个大课题,我们现在远远还没有搞明白,我们还需要深入去研究陈永贵,进而再去深入研究毛泽东、周恩来,深入研究当年主席和总理决策农业学大寨的深谋远虑。大寨人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的,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不仅是全面发展,而且是协调发展,变不可持续的发展,为可持续的发展,具有统筹规划特征的发展模式,毫无疑问体现了科学发展的含义,他们科学造田与科学种田,更是科学发展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体现。

被誉为双枪老太婆的赵洪文国,是神话还是史实?
赵老太婆双枪老太婆的诨号,不仅八十年前没有,三十年前也没有,在电影《拂晓枪声》出现之前从来没有。所有的关于她手使双枪打鬼子的故事,都是这三十年来才有的神话。神话并不可恶,不仅不可恶,有些神话还很美丽,但必须得搞清楚,神话就是神话,神话不是历史。

真实的民国——农民生活富足,地主佃户和谐共处?
但是如果你认为民国时农民的苦难仅限于经济问题,那就错了。地主的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们在农村的政治地位。农民不仅没有钱,没有权利,甚至连家里的妻女,都成为地主可以任意享用的私产。是的,你没有看错,这不是中世纪农奴制下的欧洲,而是中华民国的农村。

韩东屏:中国曾经是世界上唯一摆脱三农危机的国家
在全世界,在整个第三世界国家因绿色革命的冲击,受三农危机肆虐的年代,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却在不断向好。许多西方学者到中国来,看到中国的发展,把中国看做是第三世界的样板,人类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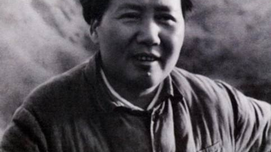
从秋收起义看毛泽东的农民情结及其启示
在以农业为主的近代中国,农民问题一直是政治家和革命家不可回避的中心问题。作为党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十分关注农民利益,并且致力于解决农民问题。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就是他探索解决农民问题的一次重要尝试,展现了他心系农民、组织农民和依靠农民的伟大情怀。

胡新民:“五七”干校的另一面
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首先就要脚踏实地劳动。领导干部,承担着特殊的责任和使命,但不是说可以讲特殊、耍特权。相反,应该坚决拒绝空谈,更加崇尚实干,带头发扬劳模精神,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通过自己的带头发扬、带头实践、带头劳动、带头创造,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带头发扬、带头实践、带头劳动、带头创造”可以说是“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要成为一种永久制度”在新时代的与时俱进。

评秦晖给地主翻案:诡辩,办不到!
租佃两大阵营的对立是不是成立,不能只看地主总计占了多少地,还应该看少地、无地贫雇农的占地情况。不能说地主占地不足40%就不会形成租、佃两个阵营,更不能说进一步“发挥”出不存在租佃两个阵营的对立与斗争!租、佃两个阵营的对垒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租佃矛盾是必然的,也是必然能走向激化的!无论秦晖先生们怎样论说地主占地占比如何的小,怎样的抹杀租、佃两个阵营的存在,“租佃关系决定论”就是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