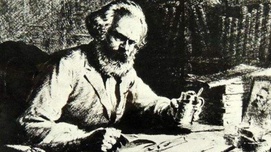
刘国光: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这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应用,更离不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制度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需要我们不断创新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正确分析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保障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调节制度,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保障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扩大开放中要始终坚持对等开放制度,保障国家的整体利益和人民利益、经济安全和制度安全;坚持用发展变化眼光看待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更高价段转变。

何干强:区分两种对立的市场、政府与国有企业观
所谓“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公平竞争”有极大的片面性,资产阶级的所谓市场公平竞争,其实只是直观地反映市场经济形态的表面关系,是用简单商品流通等价交换关系,掩盖资本主义市场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的实现环节;政府是国家的职能机关,必然具有阶级性,“政府不能进入市场”照搬了国际新自由主义的谬论,我国的人民政府理应进入市场;我国国企的本质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否定我国的国企进入市场是违反宪法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70年”学术会议成功举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程恩富学部委员认为,新中国70年历史是一个辉煌整体,可分为改革前、改革后、十八大后的新时代。这三个历史阶段是新中国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依次递进的三个发展阶段,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各种纵横比较的实证数据都证明新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也取得了辉煌绩效,不能把前后“两个三十年”割裂甚至对立起来,不能违反实证事实、有意贬低前30年的绩效来论证改革的必要性和成就。

石冀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失业问题的理论适用性
西方经济学的失业理论不具普适性,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失业问题的适用性也是一个问题,至少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失业理论对中国的失业问题具有解释意义和政策指导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若干理论创新
笔者认为,市场在一般经济资源配置中可以起决定性作用,并应更好地发挥国家在微观中观宏观宇观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应加强事先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管,建立强市场和强政府的“双强”格局;质疑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完全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论”,也不赞成第一次市场调节和第二次政府调节的时间上的“两次调节论”,而是坚持市场与国家“功能性双重调节论”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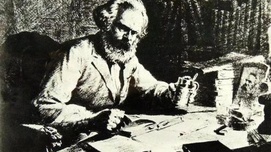
澄清一种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严重曲解
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自信,才能保证改革沿着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重启改革议程》第一作者为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诬蔑为“社会大工厂模式”,多次引用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义。马克思十分清楚地揭示了社会再生产运动与企业再生产运动的共性和区别,不可能提出把那种把企业管理放大到全社会管理的“社会大工厂模式”。该书的深层用心是,否定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指导中国当下的经济体制改革,这在改革指导思想上,造成了严重混乱。与此相关的重大理论是非,必须予以澄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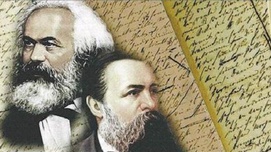
贾根良:我国应该加强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理论内部,不仅发生了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与西方正统经济学之间的尖锐对立,而且也出现了与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融合”发展的局面,“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已不能反映和容纳这种巨大变化的新情况。由于我国大学中讲授的“西方经济学”是清一色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本文将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经济学命名为“西方政治经济学”。“西方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规律的研究比“西方经济学”提供了更现实和更深刻的描述和分析,其理论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也具有直接的和重要的借鉴价值,因此,我国经济理论界应该大力加强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对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西方经济理论的本科课程设置进行改革。

国际金融危机与“新帝国主义”的腐朽表现
2008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实质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整个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下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通过经济全球化,建立最广泛的掠夺式的国际分工体系,用发展中国家创造的产品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位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顶端的美国通过美元霸权地位,掠夺他国财富,这是帝国主义寄生性或腐朽性的最隐蔽方式;通过金融国际化,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创新”,与泡沫同时泛起的是食利阶层的扩大和食利国的“繁荣”,这是帝国主义腐朽本性最集中的表现。

推动我国高校西方经济理论教学的多元化
在我国大学的本科教育中,上述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国在大规模地系统引进西方经济理论时,紧盯西方主流经济学。福山式的“历史终结论”对我国的影响,更造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唯一现代经济学的印象。

《资本论》与现代资本主义论
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批判地继承了古典主义经济学,从历史的角度全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体制,而且指出了这一体制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本文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理论基础分析了二战后现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与历史资本主义的延续性、它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过程,并进一步探讨了资本主义在发生历史性转变的同时,在国别或地域上所呈现出的多样性。

“唯心”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NO”!
在这里我要隆重推荐的是孟教授提出的“系统因果性”概念。孟教授认为,应当区分“初始原因”和“整体原因”——只有后者“才会带来系统的不可逆转”,并由此提出“有机生产方式”的思想。我以为这是极富见地的,也是很有创意的。尤其是“将不可逆转的历史性作为社会存在的根本原则”的这个观点,我认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决定论极为透彻、精准的把握。

中国股市长期积累的问题终于集中暴发,如何应对?
站在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来建立一套新的利国利民的股市制度,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一次次股灾与腐败案件,已经使中国人民对当下中国股市心寒意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不相容。股市的根本性改革,建立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股市的新“雄安”,已经是国人的普遍共识与热切期盼!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强有力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为这样的新制度创造了前提条件。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理论来源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类似的意义上面临其理论来源的问题。在我看来,它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经济学,它是我们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思想来源。其二是其他各种新兴政治经济学,国外称之为异端经济学。

大卫·M·科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美国的沉浮
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发生了重大的经济危机,即使在资本主义运行良好的时候,仍然发生了了压迫黑人、帝国主义战争等事件。这使我们一代的许多人在研究生时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尤其在美国的顶尖名校,如哈佛,耶鲁,MIT,密歇根以及我所在的伯克利。

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学
以史为鉴,忘史亡国。这一段特殊的中国经济学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势不可当,我们有这个理论自信,重铸以本土化的学术话语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同时也不排斥从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和实用价值成分中找出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以移植、借鉴和吸收的合理因素。

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大工厂模式”吗——澄清一种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严重曲解
照搬资产阶级经济学来策划“改革”的那些“权威”智囊,他们的经济思想和主张是渗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其主要表现就是公然违反我国宪法规定,搞私有化,妄图化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